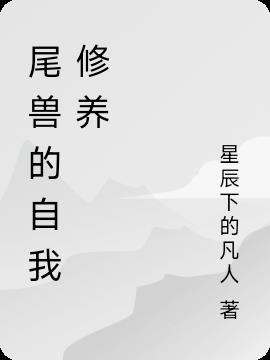少年文学>remix混音人生好看吗 > 第95章(第2页)
第95章(第2页)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干这一行?”
我刚开口,想起要把头盔上的透明罩拉上去,风猛地涌进来,吹得我眼睛睁不开。“无所谓喜不喜欢。”
“假如我非要逼着你收手,事不由人,你夹在中间会很难做吧。”
前方十字路口有个红灯,他减慢速度,融在风里的声音变清晰:“有些东西不是说收手就收得了的。”
他停下来,摸摸我的手背,“宝宝比我想法成熟呢。”
“咱们俩立场不同罢了。”
我把下巴往他肩上蹭了蹭,说,“你有分寸,就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赌,去挥霍,这没意义。”
“重要的是。”
我闭了一下嘴,话再说出口,不知怎么就降了调。“你还有我。”
“嗯?”
他不笑还好,一笑我就觉得自己蠢。这毛病怕是改不了了。
“你养我啊?”
“怎么不行,”我心一横,“等我攒几年钱,有资本开家工作室,没资本就卖唱,我会想办法的……只要你别太败家我都养得起。”
他笑了,肩膀发抖,然后松了松膀子,假装没有嘲笑我不切实际的天真。
“那敢情好。”他转弯加速,“回去我把咱们家房本啊存折啊黑账啊全部积蓄都给你,以后我就当小白脸,吃你的睡你的,上炕认识媳妇下炕认识鞋。”
“爸爸,做人不能这么不要脸。”
“反正我都快三十了,丢得起这个人。就这么定了。”
“……”
于是从那天晚上回去后他就疯了。
因为我跑回来纯粹是贸然行事,头脑冷静下来免不了有些后悔,又不好回自己家,干脆呆在录音棚弄我的翻唱。
而宫隽夜表示前天的事儿风头还没过去,他有必要在家避避嫌,闭门不见客,要么散步买猫粮,一身短袖短裤,邋邋遢遢的居家打扮,穿衬衣从不系扣子(这就很不应该了。)胡子两三天不刮,活动范围严格划分在方圆一公里内,非常听话,我让他什么时间回家就什么时间回家,要么窝在房间里听我唱歌,煞有介事的跟我探讨选曲。
我含着润喉糖,拿一份筛选过的歌单给他,二十首按照顺序全唱一遍,让他挑出合适的五首,由我收入这次的翻唱专辑里。
他坐在沙发上,手臂平摊开,嘴里叼一支圆珠笔,手中捏着我的歌单,脚尖跟随节奏打拍子,我一让他说感想,他就理直气壮地:“我哪懂你们这些人民艺术家。我唱歌跑调。”
我几欲窒息,“宫隽夜——”
“但是我认为。”
他用手指掸了掸纸面,“你对着我的时候,唱情歌最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