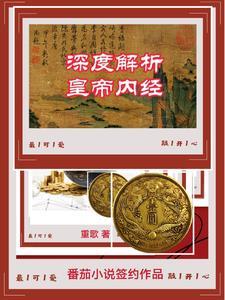少年文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原型 > 第二章 失乐园(第2页)
第二章 失乐园(第2页)
伊纹不喜欢李国华这人,不喜欢他整个砸破她和思琪怡婷的时光。而且伊纹一开始以为他老盯着她看,是跟其他男人一样,小资阶级去问无菜单料理店的菜单,那种看看也好的贪馋。但是她总觉得怪怪的,李国华的眼睛里有一种研究的意味。很久以后,伊纹才会知道,李国华想要在她脸上预习思琪将来的表情。“你们要乖乖交哦,我对女儿都没有这么大方。”她们心想,老师真幽默,老师真好。后来刘怡婷一直没有办法把《活着》看完。
思琪她们每周各交一篇作文给李国华。没有几次,李国华就笑说四个人在一起都是闲聊,很难认真检讨,不如一天思琪来他家,一天怡婷,在她们放学而他补习班还没开始上课的空当。伊纹在旁边听了也只是漠然,总不好跟邻居抢另一个邻居。这样一来,一周就少了两天见到她们,喂伤痕累累的她以精神食粮的,她可爱的小女人们。
思琪是这样写诚实的:“我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就是诚实,享受诚实,也享受诚实之后带给我对生命不可告人的亲密与自满。诚实的真意就是:只要向妈妈坦承,打破了花瓶也可以骄傲。”怡婷写:“诚实是一封见不得人的情书,压藏在枕头下面,却无意识露出一个信封的直角,像是在引诱人把它抽出来偷看。”房思琪果然是太有自尊心了。李国华的红墨水笔高兴得忘记动摇,停在作文纸上,留下一颗大红渍。刘怡婷写得也很好。她们两个人分别写的作文简直像换句话说。但是那不重要。
就是有那么一天,思琪觉得老师讲解的样子特别快乐,话题从作文移到餐厅上,手也自然地随着话题的移动移到她手上。她马上红了脸,忍住要不红,遂加倍红了。蓝笔颤抖着跌到桌下,她趴下去捡,抬起头来看见书房的黄光照得老师的笑油油的。她看老师搓着手,鹅金色的动作,她心里直怕,因为她可以想象自己被流萤似的灯光扑在身上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把老师当成男性。从不知道老师把她当成女性。老师开口了:“你拿我刚刚讲的那本书下来。”思琪第一次发现老师的声音跟颜楷一样筋肉分明,捺在她身上。
她伸手踮脚去拿,李国华马上起身,走到她后面,用身体、双手和书墙包围她。他的手从书架高处滑下来,打落她停在书脊上的手,滑行着圈住她的腰,突然束紧,她没有一点空隙寸断在他身上,头顶可以感觉他的鼻息湿湿的像外面的天空,也可以感觉到他下身也有心脏在搏动。他用若无其事的口气:“听怡婷说你们很喜欢我啊。”因为太近了,所以怡婷这句话的原意全两样了。
一个撕开她的衣服比撕开她本人更痛的小女孩。啊,笋的大腿,冰花的屁股,只为了换洗不为了取悦的、素面的小内裤,内裤上停在肚脐正下方的小蝴蝶。这一切都白得跟纸一样,等待他涂鸦。思琪的嘴在嚅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她跟怡婷遇到困难时的唇语信号。在他看来就是:婊,婊,婊,婊。他把她转过来,掬起她的脸,说:“不行的话,嘴巴可以吧。”他脸上挂着被杀价而招架无力后,搬出了最低价的店小二委屈表情。思琪出声说:“不行,我不会。”掏出来,在她的犊羊脸为眼前血筋曝露的东西害怕得张大了五官的一瞬间,插进去。暖红如洞房的口腔,串珠门帘般刺刺的小牙齿。她欲呕的时候喉咙拧起来,他的声音喷发出来:“啊,我的老天爷啊。”刘怡婷后来会在思琪的日记里读到:“我的老天爷,多不自然的一句话,像是从英文硬生生翻过来的。像他硬生生把我翻面。”
隔周思琪还是下楼。她看见书桌上根本没有上周交的作文和红蓝笔。她的心跟桌面一样荒凉。他正在洗澡,她把自己端在沙发上。听他淋浴,那声音像坏掉的电视机。他把她折断了扛在肩膀上。捻开她制服上衣一颗颗纽扣,像生日时吹灭一支支蜡烛,他只想许愿却没有愿望,而她整个人熄灭了。制服衣裙踢到床下。她看着衣裳的表情,就好像被踢下去的是她。他的胡楂磨红、磨肿了她的皮肤,他一面说:“我是狮子,要在自己的领土留下痕迹。”她马上想着一定要写下来,他说话怎么那么俗。不是她爱慕文字,不想想别的,实在太痛苦了。
她脑中开始自动生产譬喻句子。眼睛渐渐习惯了窗帘别起来的卧室,窗帘缝隙漏进些些微光。隔着他,她看着天花板像溪舟上下起伏。那一瞬间像穿破了小时候的洋装。想看进他的眼睛,像试图立在行驶中的火车,两节车厢连接处,那蠕动肠道写生一样,不可能。枝状水晶灯围成圆形,怎么数都数不清有几支,绕个没完。他绕个没完。生命绕个没完。他趴在她身上狗嚎的时候,她确确实实感觉到心里有什么被他捅死了。在她能够知道那个什么是什么之前就被捅死了。他撑着手,看着她静静地让眼泪流到枕头上,她湿湿的羊脸像新浴过的样子。
李国华躺在床上,心里猫舔一样轻轻地想,她连哭都没有哭出声,被人奸了还不出声,贱人。小小的小小的贱人。思琪走近她的衣服,蹲下来,脸埋在衣裙里。哭了两分钟,头也没有回过去,咬牙切齿地说:“不要看我穿衣服。”李国华把头枕在手上,射精后的倦怠之旷野竟有欲望的芽。不看,也看得到她红苹果皮的嘴唇,苹果肉的乳,杏仁乳头,无花果的隐秘所在。中医里健脾、润肠、开胃的无花果。为他的搜藏品下修年代的一个无花果。一个觉得处女膜比断手断脚还难复原的小女孩,放逐他的欲望,钓在杆上引诱他的欲望走得更远的无花果。她的无花果通向禁忌的深处。她就是无花果。她就是禁忌。
她的背影就像是在说她听不懂他的语言一样,就像她看着湿黏的内裤要不认识了一样。她穿好衣服,抱着自己,钉在地上不动。
李国华对着天花板说:“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不要生我的气,你是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美丽是不属于它自己的。你那么美,但总也不可能属于全部的人,那只好属于我了。你知道吗?你是我的。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气。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勇气才走到这一步。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小天使。你知道我读你的作文,你说:‘在爱里,我时常看见天堂。这个天堂有涮着白金色鬃毛的马匹成对地亲吻,一点点的土腥气蒸上来。’我从不背学生的作文,但是刚刚我真的在你身上尝到了天堂。一面拿着红笔我一面看见你咬着笔杆写下这句话的样子。你为什么就不离开我的脑子呢?你可以责备我走太远。你可以责备我做太过。但是你能责备我的爱吗?你能责备自己的美吗?更何况,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节礼物。”她听不听得进去无所谓,李国华觉得自己讲得很好。平时讲课的效果出来了。他知道她下礼拜还是会到。下下个礼拜亦然。
思琪当天晚上在离家不远的大马路上醒了过来。正下着滂沱大雨,她的制服衣裙湿透,薄布料紧抱身体,长头发服了脸颊。站在马路中央,车头灯来回笞杖她。可是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的门,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她以为她从李老师那儿出来就回了家。或者说,李老师从她那儿出来。那是房思琪第一次失去片段记忆。
那天放学思琪她们又回伊纹一维家听书。伊纹姐姐最近老是恹恹的,色香味俱全的马尔克斯被她念得五蕴俱散。一个段落了,伊纹跟她们讲排泄排遗在马尔克斯作品的象征意义。伊纹说:“所以说,屎在马尔克斯的作品里,常常可以象征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的荒芜感,也就是说,排泄排遗让角色从生活中的荒芜见识到生命的荒芜。”怡婷突然说:“我现在每天都好期待去李老师家。”那仿佛是说在伊纹这里只是路过,仿佛是五天伊纹沾一天李老师的光。怡婷一出口马上知道说了不该说的话。但伊纹姐姐只说:“是吗?”继续讲马尔克斯作品里的尿与屎,可是口气与方才全两样了,伊纹姐姐现在听上去就像她也身处在马尔克斯的作品里便秘蹲厕所一样。思琪也像便秘一样涨红了脸。怡婷的无知真是残酷的。可也不能怪她。没有人骑在她身上打她。没有人骑在她身上而比打她更令她难受。她们那时候已经知道了伊纹姐姐的长袖是什么意思。思琪讨厌怡婷那种为了要安慰而对伊纹姐姐加倍亲热的神色,讨厌她完好如初。
思琪她们走之后,许伊纹把自己关在厕所,扭开水龙头,脸埋在掌心里直哭。连孩子们都可怜我。水龙头哗啦哗啦响,哭了很久,伊纹看见指缝间泄漏进来的灯光把婚戒照得一闪一闪的。像一维笑眯眯的眼睛。
喜欢一维笑眯眯。喜欢一维看到粉红色的东西就买给她,从粉红色的铅笔到粉红色的跑车。喜欢在视听室看电影的时候一维抱着家庭号的冰淇淋就吃起来,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肩窝说这是你的座位。喜欢一维一款上衣买七种颜色。喜欢一维用五种语言说我爱你。喜欢一维跟空气跳华尔兹。喜欢一维闭上眼睛摸她的脸说要把她背起来。喜欢一维抬起头问她一个国字怎么写,再把她在空中比画的手指拿过去含在嘴里。喜欢一维快乐。喜欢一维。可是,一维把她打得多惨啊!
每天思琪洗澡都把手指伸进下身。痛。那么窄的地方,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有一天,她又把手伸进去的时候,顿悟到自己在干什么:不只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自己的童年。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丢弃了,那他就不能再丢弃一次。反正我们原来就说爱老师,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
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说不定真与假不是相对,说不定世界上存在绝对的假。她被捅破、被刺杀。但老师说爱她,如果她也爱老师,那就是爱。做爱。美美地做一场永夜的爱。她记得她有另一种未来,但是此刻的她是从前的她的赝品。没有本来真品的一个赝品。愤怒的五言绝句可以永远扩写下去,成为上了千字还停不下来的哀艳古诗。老师关门之际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说:“嘘,这是我们的秘密哦。”她现在还感觉到那食指在她的身体里既像一个摇杆也像马达。遥控她,宰制她,快乐地咬下她的宿痣。邪恶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爱老师不难。
人生不能重来,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把握当下。老师的痣浮在那里,头发染了就可以永远黑下去,人生不能重来的意思是,早在她还不是赝品的时候就已经是赝品了。她用绒毛娃娃和怡婷打架,围着躺在湿棉花上的绿豆跳长高舞,把钢琴当成凶恶的钢琴老师,怡婷恨恨地捶打低音的一端,而她捶打出高音,在转骨的中药汤里看彼此的倒影,幻想汤里有独角兽角和凤凰尾羽,人生无法重来的意思是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日后能更快学会在不弄痛老师的情况下帮他摇出来。意思是人只能一活,却可以常死。这些天,她的思绪疯狂追猎她,而她此刻像一只小动物在畋猎中被树枝拉住,逃杀中终于可以松懈,有个借口不再求生。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思琪在浴室快乐地笑出声音,笑着笑着,笑出眼泪,遂哭起来了。
还不到惯常的作文日,李国华就去按房家的门铃。思琪正趴在桌上吃点心,房妈妈把李国华引进客厅的时候,思琪抬起头,眼睛里没有眼神,只是盯着他看。他说,过道的小油画真美,想必是思琪画的。他给思琪送来了一本书。他跟房妈妈说:“最近城市美术馆有很棒的展览,房先生房太太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带思琪去?反正我是没缘了,我家晞晞不会想去。”房妈妈说:“那刚好,不如老师你帮我们带思琪去吧,我们夫妻这两天忙。”李国华装出考虑的样子,然后用非常大方的口气答应了。房妈妈念思琪:“还不说谢谢,还不去换衣服?”思琪异常字正腔圆地说了:“谢谢。”
刚刚在饭桌上,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拿了老师的书就回房间。锁上房间门,背抵在门上,暴风一样翻页,在书末处发现了一张剪报。她的专注和人生都凝聚在这一张纸上,直见性命。剪的是一个小人像,大概是报纸影剧版剪下来的。一个黑长头发的漂亮女生。思琪发现自己在无声地笑。刘墉的书,夹着影剧版的女生。这人比我想的还要滑稽。
后来怡婷会在日记里读到:“如果不是刘墉和影剧版,或许我会甘愿一点。比如说,他可以用阔面大嘴的字,写阿伯拉写给哀绿绮思的那句话:你把我的安全毁灭了,你破坏了我哲学的勇气。我讨厌的是他连俗都懒得掩饰,讨厌的是他跟中学男生没有两样,讨厌他以为我跟其他中学女生没有两样。刘墉和剪报本是不能收服我的。可惜来不及了。我已经脏了。脏有脏的快乐。要去想干净就太苦了。”
思琪埋在衣柜里千头万绪,可不能穿太漂亮了,总得留些给未来。又想,未来?她跪在一群小洋装间,觉得自己是柔波上一座岛。出门的时候房妈妈告诉思琪,老师在转角路口的便利商店等她。也没叮嘱她不要太晚回家。出了大楼才发现外面下着大雨,走到路口一定湿透了。算了。愈走,衣裙愈重,脚在鞋子里,像趿着造糟了的纸船。像拨开珠帘那样试着拨开雨线,看见路口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顶有无数的雨滴溅开成琉璃皿。坐进后座的时候,先把脚伸在外面,鞋子里竟倒出两杯水。李国华倒是身上没有一点雨迹安坐在那里。
老师看上去是很喜欢她的模样的意思,微笑起来的皱纹也像马路上的水洼。李国华说:“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的中国人物画历史吧,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思琪快乐地说:“我们隔了一个朝代啊。”他突然趴上前座的椅背,说:“你看,彩虹。”而思琪往前看,只看到年轻的出租车司机透过后视镜看了他们一眼,眼神像钝钝的刀。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像他们眼中各自的风景一样遥远。出租车直驶进小旅馆里。
李国华躺在床上,头枕在双手上。思琪早已穿好衣服,坐在地上玩旅馆地毯的长毛,顺过去摸是蓝色的,逆过来摸是黄色的,那么美的地毯,承载多少猥亵的记忆!她心疼地哭了。他说:“我只是想找个有灵性的女生说说话。”她的鼻孔笑了:“自欺欺人。”他又说:“许想写文章的孩子都该来场畸恋。”她又笑了:“借口。”他说:“当然要借口,不借口,你和我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吗?”李国华心想,他喜欢她的羞恶之心,喜欢她身上冲不掉的伦理,如果这故事拍成电影,有个旁白,旁白会明白地讲出,她的羞耻心,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射进她幽深的教养里。用力揉她的羞耻心,揉成害羞的形状。
隔天思琪还是拿一篇作文下楼。后来李国华常常上楼邀思琪看展览。
怡婷很喜欢每周的作文日。单独跟李老师待在一起,听他讲文学人物的掌故,怡婷都有一种面对着满汉全席无下箸处的感觉。因为不想要独享老师的时间被打扰,根据同理心,怡婷也从未在思琪的作文日敲老师家的门。唯一打搅的一次,是房妈妈无论如何都要她送润喉的饮料下去给老师。天知道李国华需要润滑的是哪里。
老师应门的神色比平时还要温柔,脸上播报着一种歌舞升平的气象。思琪趴在桌上,猛地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怡婷。怡婷马上注意到桌上没有纸笔。思琪有一种悲壮之色,无风的室内头发也毛糟糟的。李国华看了看思琪,又转头看了看怡婷,笑笑说:“思琪有什么事想告诉怡婷吗?”思琪咬定颤抖的嘴唇,最后只用唇语对怡婷说:“我没事。”怡婷用唇语回:“没事就好,我以为你生病了,小笨蛋。”李国华读不出她们的唇语,但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在思琪身上发酵的屈辱感有信心。
三个人围着桌坐下来,李国华笑笑说:“你一来我都忘记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他转过去,用慈祥的眼神看思琪。思琪说:“我也忘了。”三个人的聊天泛泛的。思琪心想,如果我长大了,开始化妆,在外头走一天,腮红下若有似无的浮油一定就是像现在这样的谈话,泛泛的。长大?化妆?思想伸出手就无力地垂下来。她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前年教师节那时候就已经死了。思琪坐在李老师对面,他们之间的地板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快乐仿佛要破地萌出,她得用脚踩紧地面才行。
怡婷说道:“孔子和四科十哲也是同志之家啊。”李老师回她:“我可不能在课堂上这样讲,一定会有家长投诉。”怡婷不甘心地继续说:“一整个柏拉图学园也是同志之家啊。”“思琪?”听他们欢天喜地地说话,她突然发现满城遍地都是幸福,可是没有一个属于她。“思琪?”“哦!对不起,我没听见你们说什么。”思琪感觉脸都锈了,只有眼睛在发烧。李国华也看出来了,找了个借口温柔地把怡婷赶出去。
房思琪的快乐是老师把她的身体压榨出高音的快乐。快乐是老师喜欢看她在床上浪她就浪的快乐。佛说非非想之天,而她在非非爱之天,她的快乐是一个不是不爱的天堂。她不是不爱,当然也不是恨,也绝不是冷漠,她只是讨厌极了这一切。他给她什么,是为了再把它拿走。他拿走什么,是为了高情慷慨地还给她。一想到老师,房思琪便想到太阳和星星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她便快乐不已,痛苦不堪。李国华锁了门之后回来吮她的嘴:“你不是老问我爱不爱你吗?”房思琪拔出嘴以后,把铁汤匙拿起来含,那味道像有一夜她睡糊了整纸自己的铅笔稿,两年来没人看没人改她还是写的作文。
他剥了她的衣服,一面顶撞,一面说:“问啊!问我是不是爱你啊!问啊!”完了,李国华躺下来,优哉地闭上眼睛。思琪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穿好了衣服,像是自言自语说道:“以前伊纹姐姐给我们念《百年孤独》,我只记得这句─如果他开始敲门,他就要一直敲下去。”李国华应道:“我已经开门了。”思琪说:“我知道。我在说自己。”李国华脑海浮现伊纹的音容,心里前所未有地平静,一点波澜没有。许伊纹美则美矣,他心里想,可自己从没有这么短时间里两次,还是年纪小的好。
一次怡婷的作文课结束,老师才刚出门,怡婷就上楼敲房家的门。思琪开的门,没有人在旁边,可是她们还是用她们的唇语。怡婷说:“我发现老师就是好看在目如愁胡。”“什么?”“目如愁胡。”“听不懂。”“哀愁的愁,胡人的胡。”思琪没接话。“你不觉得吗?”“我听不懂。”怡婷撕了笔记本写给思琪看:目如愁胡。“深目蛾眉,状如愁胡,你们还没教到这边吗?”怡婷盯着思琪看,眼中有胜利者的大度。“还没。”“老师好看在那一双哀愁的胡人眼睛,真的。你们可能下礼拜就教到了吧。”“可能吧,下礼拜。”
思琪她们整个中学生涯都有作文日陪着。作文日是枯燥、不停绕圈子的读书生活里的一面旗帜。对于怡婷来说,作文日是一个礼拜光辉灿烂的开始。对思琪而言,作文日是长长的白昼里一再闯进来的一个浓稠的黑夜。
刚过立秋,有一天,怡婷又在李国华那里,思琪跑来找伊纹姐姐。伊纹姐姐应门的眼睛汪汪有泪,像是摸黑行路久了,突然被阳光刺穿眼皮。伊纹看起来好意外,是寂寞惯的人突然需要讲话,却被语言落在后头的样子,那么幼稚,那么脆弱。第一次看见伊纹姐姐脸上有伤。思琪不知道,那是给一维的婚戒刮的。她们美丽、坚强、勇敢的伊纹姐姐。
两个人坐在客厅,一大一小,那么美,那么相像,像从俄罗斯娃娃里掏出另一个娃娃。伊纹打破沉默,皱出酒窝笑说:“今天我们来偷喝咖啡好不好?”思琪回:“我不知道姐姐家里有咖啡。”伊纹的酒窝出现一种老态:“妈妈不让我喝,琪琪亲爱的,你连我家里有什么没有什么都一清二楚,这下我要害怕了哦。”第一次听见伊纹姐姐用叠字唤她。思琪不知道伊纹想唤醒的是她或者自己的年轻。
伊纹姐姐开粉红色跑车载思琪,把敞篷降下来,从车上招呼着拂过去的空气清新得不像是这城市的空气。思琪发现她永远无法独自一人去发掘这个世界的优雅之处。初一的教师节以后她从未长大。李国华压在她身上,不要她长大。而且她对生命的上进心,对活着的热情,对存在原本圆睁的大眼睛,或无论叫它什么,被人从下面伸进她的身体,整个地捏爆了。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道家的无,也不是佛教的无,是数学上的无。零分。伊纹在红灯的时候看见思琪脸上被风吹成横的泪痕。伊纹心想,啊,就像是我躺在床上流眼泪的样子。
伊纹姐姐开口了,声音里满是风沙,沙不是沙尘砂石,在伊纹姐姐,沙就是金矿金沙。“你要讲吗?”忍住没有再唤她琪琪,她刚刚那样叫思琪的时候就意识到是不是母性在作祟。沉默了两个绿灯、两个红灯,思琪说话了:“姐姐,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讲。”一整个积极的、建设的、怪手砂石车的城市围观她们。伊纹说:“不要对不起。该对不起的是我。我没有好到让你感觉可以无话不谈。”思琪哭得更凶了,眼泪重到连风也吹不横,她突然恶声起来:“姐姐你自己也从未跟我们说过你的心事!”一瞬间,伊纹姐姐的脸悲伤得像露出棉花的布娃娃,她说:“我懂了。的确有些事是没办法讲的。”思琪继续骂:“姐姐你的脸怎么会受伤!”伊纹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跌倒了。说来说去,还是我自己太蠢。”思琪很震惊,她知道伊纹正在告诉她真相。伊纹姐姐掀开譬喻的衣服,露出譬喻丑陋的裸体。她知道伊纹知道她一听就会明白。脸上的刮伤就像是一种更深邃的泪痕。思琪觉得自己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
思琪一面拗着自己的手指一面小声说话,刚刚好飘进伊纹姐姐的耳朵之后就会被风吹散的音量,她说:“姐姐,对不起。”伊纹用一只手维持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一只手抚摸她的头发,不用找也知道她的头的位置。伊纹说:“我们都不要说对不起了,该说对不起的不是我们。”车子停在商店街前面,以地价来看,每一间商店的脸都大得豪奢。跑车安全带把她们绑在座位上,如此安全,安全到心死。思琪说:“姐姐,我不知道决定要爱上一个人竟可以这么容易。”伊纹看着她,望进去她的眼睛,就像是望进一缸可鉴的静水,她解开安全带,抱住思琪,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我可怜的琪琪。”她们是一大一小的俄罗斯娃娃,她们都知道,如果一直剖开、掏下去,掏出最里面、最小的俄罗斯娃娃,会看见娃娃只有小指大,因为它太小,而画笔太粗,面目遂画得草率,哭泣般面目模糊了。
她们进去的不是咖啡厅,而是珠宝店。眯起眼睛四顾,满屋子亮晶晶的宝石就像是四壁的橱窗里都住着小精灵在眨眼睛。假手假脖子也有一种童话之意。一个老太太坐在橱窗后面,穿着洋红色的针织洋装,这种让人说不清也记不得的颜色和质料,像是在说: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不是。洋红色太太看见伊纹姐姐,马上摘下眼镜,放下手边的宝石和放大镜,对伊纹说:“钱太太来了啊,我上去叫毛毛下来。”遂上楼了,动作之快,思琪连楼梯在哪里都看不出来。思琪发现老太太也没有先把桌上的宝石收起来。伊纹姐姐低声跟思琪说:“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这里有一台跟你一样大的冰滴咖啡机器哦。”
一个蓝色的身影出现,一个戴着全框眼镜的圆脸男人,不知道为什么让人一眼就感觉他的白皮肤是牙膏而非星沙的白,蓝针织衫是计算机荧幕而不是海洋的蓝。他上唇之上和下唇之下各蓄着小小一撮胡子,那圆规方矩的胡子有一种半遮嘴唇的意味。思琪看见伊纹姐姐把脸转过去看向他的时候,那胡子出现了一片在等待人躺上去的草皮的表情。毛毛先生整个人浴在宝石小精灵的眼光之雨中,他全身上下都在说: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不是。那是早已停止长大的房思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对一个人。
中学结束的暑假前,思琪她们一齐去考了地方一女中和台北的一女中,专考语文资优班。两人两头都上榜了。房妈妈刘妈妈都说有对方女儿就不会担心自己女儿离家在外。李国华只是聚餐的时候轻描淡写两句:“我忙归忙,在台北的时候帮忙照看一下还是可以的。”李老师的风度气派给房妈妈刘妈妈喂了定心丸。思琪在聚餐的圆桌上也并不变脸,只是默默把寿司下不能食用的云纹纸吃下去。
整个升高中前的暑假,李老师都好心带思琪去看展览。有一次,约在离她们的大楼甚远的咖啡厅。看展的前一天,李国华还在台北,思琪就先去咖啡厅呆坐着。坐了很久,她才想到这倒像是她在猴急。像一个男人等情人不到,干脆自己点一瓶酒喝起来,女人到之前,酒早已喝完,只好再叫一瓶,女人到了之后,也无从解释脸红心跳从哪里来。就要急。
思琪的小圆桌突然印上一个小小的小小的黑影子,影子缓缓朝她的咖啡杯移动。原来是右手边的落地窗外沾着一只苍蝇,被阳光照进来。影子是爱心形状,想是蝇一左一右张着翅膀。桌巾上的碎花图案整齐得像秧苗。影子仿佛游戏一样穿梭在花间,一路游到她的咖啡盘,再有点痛苦似的扭曲着跳进咖啡里,她用汤匙牵起一些奶泡哄弄那影子,那影子竟乖乖停住不动。她马上想到李国华一面扪着她,一面讲给她听,讲汉成帝称赵飞燕的胸乳是温柔乡。那时候她只是心里反驳:说的是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吧?不知道自己更想反驳的是他的手爪。思琪呆呆地想,老师追求的是故乡,一个只听不说、略显粗蠢、他自己也不愿承认为其粗蠢感到安心的,家乡?影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游出她的咖啡杯,很快地游向她,就从桌沿跳下去了。她反射地夹了一下大腿。她穿的黑裙子,怎么样也再找不到那影子。望窗上一看,那蝇早已经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