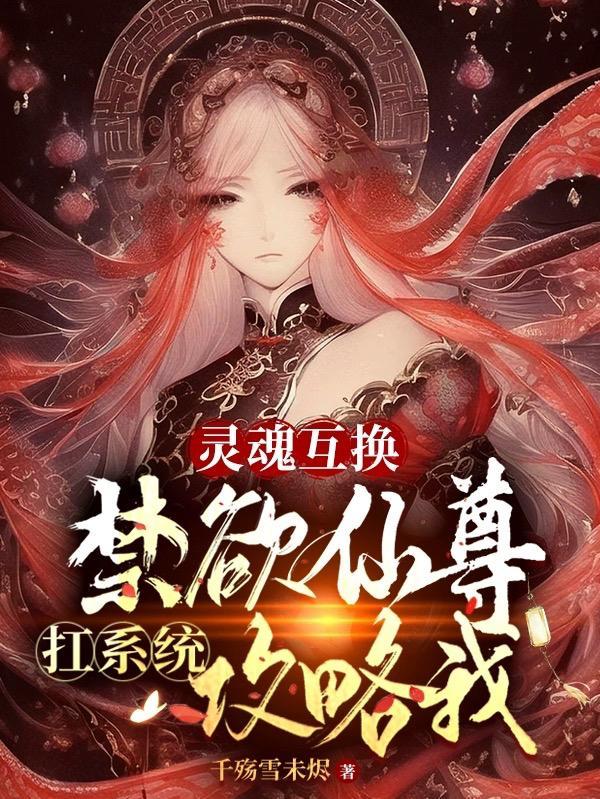少年文学>重生之将女为帝 喵圆喵 > 第50章(第2页)
第50章(第2页)
一切都不再重要。
棋局已然成型,困在其中的棋子,只能是顺着棋手的思路,落向固定的某处。
不想做棋子,便只能成为棋手!
温哲翰监国第二日,晏清收到了王淑语的拜帖。
晏清没应。
同一天,镇南侯府递了邀请函。
晏清依旧婉拒。
山海居书房内,晏清静默地坐着。
燕七来来去去,将康都城内的动向,尽皆说与她听。
那些闭府养病的官眷们,好似忽然都病好了,四下里互相走动。
今天这个家里有个茶会,明天那个家里有个诗会。
静默了几个月的康都城,像是忽然活过来了一样。
整个康都城都泛发出一种久违的生机昂扬之态,除了六皇子刚去世皇帝病重的皇宫,以及端王府、肃王府和半年之内两次出殡的镇西侯府。
温哲翰监国第七日,六皇子头七,一直闭府的镇西侯府却突然开了府门。
一辆青棚小车自偏门出来,一路往城外去。
车中晏清攥着暗卫自佛安寺送回来的信纸,两眼通红,胸腔因怒极而剧烈起伏。
青衣缩在一旁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晏清,双手紧扣着车板,耷拉着脑袋。
“对不起……”
青衣小声地道歉,“对不起……”
晏清沉下心中那一口气,沙哑着嗓子开口:“不是你的错。”
胡言乱语
佛安寺西厢房,晏清推开房门,看着端坐在首位悠闲喝茶的人,脸色黝黑。
不是温哲茂,却也是她前世的老熟人——温哲茂的谋士司惗。
隐士司惗长居肃王府,不曾出来走动,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温哲茂的人。
晏清沉着双眸,压着怒气,冷声开口:“我来了,放我娘走。”
“哈哈哈,不急,不急。”
司惗笑道,斟一杯茶,请晏清,“小将军舟车劳顿,且坐下饮杯清茶。”
晏清盯着他,但司惗始终带着笑,恍若未闻,自在地喝自己的茶,还同晏清诉说自己的感想:“都说佛安寺的银云雪尖,是茶中一绝。今日得饮,确实如此啊!”
站了半盏茶的功夫,见司惗丝毫没有开口的打算,晏清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坐到了案几另一侧,却没饮茶。
“你想怎么样?”
晏清咬着牙问。
司惗饮一口茶,咂吧下嘴,似在回味茶得甘甜可口,直等到晏清拳头都攥起来了,他才转过脸来,皮笑肉不笑地反问:“小将军不问我是谁?”
晏清心中一跳,但面上怒气不减,一拍桌子蹿起来攥着司惗的衣襟就把人提了起来,冷声驳斥:“我管你是谁!敢动我娘,我扒了你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