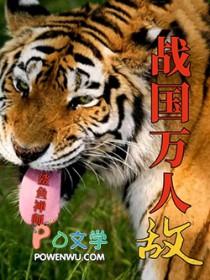少年文学>千屿千寻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只是走了两步,徐千屿从后面追上来,拉住他袖子,随即一只手探进来,似乎在摸索着他的手。
刚才帮她调息,想必她得了些趣味,一松开,便又躁起来了。沈溯微眼睫一动,没做声,一把反握住她的手。
徐千屿见素来温柔的王夫人忽而撇下她,焦躁气恼,但王夫人默然将她牵住,她又安定踏实下来,便任她拉着走了。说来也奇,一路上竟畅通无阻,都没遇到一个人盘问一句。
二人出门不久,小冬从阁子里追出来。
自上次做噩梦以后,她总是睡不踏实,半夜要醒来一回,悄悄掀开帘子看小姐还在不在。
今日小姐又不见了。她打开角门时,看见远处有两个影子。又去东厢房敲开门问了问,确认小姐应当是和王夫人一起走了。
虽说小姐有伴,可大半夜的,两个柔弱女子,到底叫人担心。小冬拿不准主意,便叫松柏起来。
松柏一听小姐是和王夫人一起往东边走了,一面穿衣一面道:“坏了,恐怕是回王长史府上了。”
“王长史府上?”
“那王长史,不是个好人。”松柏说,“他家还有好多凶巴巴的家丁。”
小冬登时花容失色:“那怎么办,小姐没带人,万一在那处吃亏。”
“我去叫观娘。”松柏蹬上鞋子就要走。
“别,小姐虽胆大但不冒失,万一是同那边说好的,不想惊动观娘和老爷才半夜而行。明天就是小姐生辰了,大喜的日子,别闹她不愉快。”
“那你说呢?”
小冬提起灯笼,澄黄的光照在她决断的脸上。上次小姐说什么都不让她出门,硬把她一人留下,叫她难过了许久。她哪有那么胆小?
“你跟我说王长史府在哪,我们悄悄跟上,再拿一束炮,和院里人商量个暗号。倘若没事,我们顺便将小姐接回来,也不惊动他人;倘若是有事,便点一簇‘满天星’,叫人增援。”
松柏一听,也觉得有理:“走,我和你一道。”
徐千屿随着王夫人长驱直入王长史府,仍然无人阻拦,不由得诧异。但方才路上,王夫人和她约法三章,叫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多话,最好是不说话。
徐千屿也知道,自己开口,可能会将事情搅闹得不可收拾,看在王夫人恳求的份上,不情愿地闭了嘴。
二人走进一个很暗的阁子,桌案上只有一盏微弱的烛,那光甚至没有窗户透出的月光亮。桌案上整齐地摆有书卷,纸张,砚台,又悬一排笔,披着幽暗的月色。大约是书房。
王夫人松开她,仰头查看门窗,柜子。视线扫过一遍后,坐在了案前。
徐千屿无聊,看见书桌上摆着几个敞开的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东西。便拿出来瞧,里面装的竟然是崭新的绣花鞋垫。那针脚密密匝匝,绣工细致精美,每一朵花都好看,徐千屿一片一片翻看,竟然绣满了十二月令花。
另一个盒子里也是绣品,各式各样的手工制的抹额,摸起来柔软又舒服。
徐千屿不禁问:“这都是你绣的?”
难以想象,那双清冷无情的眼睛,也能在灯下日复一日补着这样的针脚。
王夫人垂眸瞥了一眼千屿手上绣品,却没有作声,似是默认。
“你怎么回来了?”
背后忽传来人声。徐千屿一惊,回头,竟是王端站在书房门口。
月光照着他病气苍白的面孔,显得他眼眶更红,他惊讶地望向王夫人,神色有些焦躁。
“妾有东西……”
“什么东西?取了便快走吧。”王端急促地打断,他站在门口,胸口起伏,俨然是用力忍耐着咳嗽。
王夫人却没有起身:“你我夫妻一场,缘何如此提防。”
“我们已经……咳咳……和离了,算得什么夫妻。”王端手抚胸口,随着剧烈的咳嗽,他额角那蜘蛛网样的青筋越发明晰,似能看到青紫色的血管一鼓一鼓地跳动,仿佛要挣脱皮肤而出,“再不出去,我便……报官了,告你一个私闯官邸,入室盗窃。”
王夫人站了起来,竟笑道:“好,那你去啊。”
徐千屿让她反手一拉,便按坐在椅上。
她一步步朝王端走去,幽柔之气数步内便被莫名的清寒取代,如身携料峭西风,气势忽而变得压人至极。
王端眼睁睁看她靠近,于口中挣出一声虚弱的低吟:“月吟,走吧。”
王夫人走到面前,将他当胸轻轻一推,竟推得他踉跄后退几步。王夫人道:“夫妻间事,不当小儿面说,我们去外面。”
说罢,回眸看了徐千屿一眼。徐千屿忽觉这屋子瑟然生寒,两肩似有一对掌一压而下,将她按在椅上,动弹不得。
王端第二只脚马上要退出门槛。
变故在此时陡然发生。
一个提着灯的人影从后面跑来,那澄黄的灯笼光忽而照亮了王端半张惨白的脸。
王端像畏光一般,眼睛忽而瞪大,而瞳子霎时缩小。随后那蜘蛛网一般的青筋毫无征兆地挣开皮肤,于王端惨白的面孔侧边,血淋淋剥离出了另一颗“头”:这脑袋没有五官,黑黝黝的黑气暴涨,野兽般暴怒地张开大口,反身一口便将来人吞吃入腹!
同时,“王夫人”袖中金剑迸射而出,一分为三:一把钉入王端胸口,一把钉入腹部,将其狠钉在墙上;另有一把“噗嗤”一声将那黑气构成的脑袋从颈上贯穿。魔物不及咀嚼,受力张嘴,“哇”一下,又将人囫囵个儿地吐了出来。
松柏跑近了,瞧见地上的人,来不及点上“满天星”便腿一软跪倒在地:“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