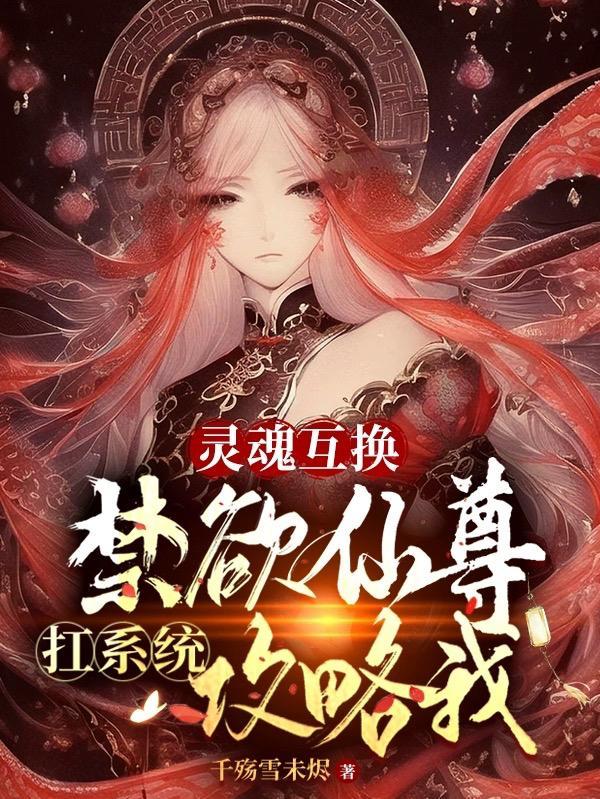少年文学>殿下他好像不行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那时已近深夜,想着祖父得早些休息,他便没有追问。
此时他心念一转,立即膝盖一弯,作势往下跪:“末将轻狂,举止无端,向殿下赔罪!”
从前几日的相处来看,恭王为人随和、不拘小节。他原本以为自己作出了姿态,恭王便会相扶;谁知与此同时恰巧一阵风来,恭王微咳,不由抬手掩口——于是他便扑通一声,结结实实跪到地上,压起一片草灰。
刘希恕小算盘落个空,再抬眼看时,恭王已然笑着伸手拉他:“何须如此,区区小事罢了。军营之中不必拘着那些虚礼!”
恭王脸上笑容格外灿烂。
刘希恕本有些郁闷,被这么对面一笑,只觉心眼俱开,顿时觉得跪他也没什么大不了。他倒不忘转头恨恨剜一眼谢承泽:我都跪了,你不跪?!
不料谢承泽正盯着恭王愣神,没看见他的眼色。
我跟这小子没完。刘希恕想,默默在心里的小算盘上记下谢承泽这一笔。
他随即便道:“末将也是为城防着想,那些人不能放进城来!”
作为一营主将,常思明再怎么也得说话了,叹了一声:“都是妇孺……刘将军你刚到不晓得,那些小儿虽名义上没有父亲,但左不过是大魏人的种。要说留在城外任其自生自灭,确实于心不忍……”
刘希恕并没把常思明放在眼里,但听他这语气,本欲再说也只好闭嘴。
谢承泽一双亮亮眼睛看着萧彦,满是期待。
若说实话,萧彦对此时滞留城外的人并不在意。刘希恕年纪虽不大,说的却是实情,口粮不够,城内百姓与军营都举步维艰,此时再放北边的人进来的确不妥。若出了事情,少不得要他担着;但被这么一双眼睛看着,他不由松了口:“既是如此,便允许孩童可自由出入;超过车辙高的人,不论男女,都不得放进来。”
这个方案算是折中,刘希恕和常思明都没话说,表示遵命。但谢承泽显然不满意,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只低着头。
乐季以为此事便翻过了。到了晚间,见主子似乎一直在想事,便提醒道:“殿下,洗脚水都快凉了吧?”
萧彦这才回神。
旁人不知,其实行止端肃的恭王一双足生得极是秀气,白皙瘦削,脚趾纤长;这段时日走动多些,脚底长出薄茧,秀美中透出坚韧,倒愈发生动。
简陋床帐的灯下,隐约看得见脚面皮肤下的细细青筋,更显莹白。
乐季不由后退一步,微微转脸移开视线。乐孟近前递上擦脚棉巾,就听萧彦忽然道:“给府里去急信,支些钱买粮,给那些女人。”
乐孟没明白:“什么女人?”
乐季知道他说的是白日里的事,劝道:“殿下这又何必,动用私银赈济,让首阳那边知道,恐要说您邀买人心,叫朝中难堪……”
萧彦摆手:“所以,你悄悄去做,别让人知晓。”
乐季更加不懂:“如此,连那些边民妇孺也不会念您的好,还白白落个把柄。”
萧彦不再说话,径自躺下。乐季便知他主意已定,只好退下。
萧彦放下床帐,自嘲一笑。他何尝不知道这些?只是抵不住白日里谢承泽失落的模样罢了。
前世欠的,今世不由得不还。
抓绑
也许是赌气,谢承泽自行请命,得了常思明准许,次日天不亮便带了一队精锐轻骑出城继续往北搜寻犬戎退兵的下落。萧彦每日晨起例行巡营时,只见到枣核独自在营旁刺棘丛边无聊地扑逮沙虫。
跟在后面的乐孟见他脚步略略一顿,朝平日回房不同的方向走,便问:“殿下这是想出营?”
萧彦随意点头:“去城中瞧瞧。”
乐季此时本该去协助刘希恕清点军务,听得他要出营便也要跟上。萧彦对他另有吩咐:“去看看那刘家小子,本王瞧他虽是纨绔,倒也算能做点事情。北军这边不少人看他不顺眼,大局为重,别叫人给他使太多绊子误了事。”
乐季不放心:“那殿下再带个人,城中不比营里安全。”
萧彦并不停步,侧身露出腰间佩剑示意:“光天白日,本王还能丢了不成。”
乐孟快步跟上,同时对乐季摆拱拱手,表情滑稽:信不过我?
乐季便只好作罢。
谁知不过三炷香功夫,乐孟便气急败坏地冲回来,把他拽到僻静处,脸上的表情仿佛天要塌了:“殿下、殿下不见了!”
见乐季立起眉毛瞪他,便压低声音:“我们去的是城外那些游民那边……我一直紧紧跟着的,不过错了个眼,他就……不见了!”
乐季勉强保持镇定:“许是去城中其他地方了?”
乐孟慌得全然失了分寸,丈八男儿摇头如拨浪鼓:“不会,游民那地方虽乱但无遮无挡,他若回城我不可能看不到!我回来问过,他并没有回营!”
乐季瞧他这神色,心中一揪,下意识地攥紧佩刀刀柄,果断道:“那你还等什么!走,带人把那游民地的人尽数拘来审问!”
出于某种微妙心理——谢承泽不在,想替他照拂游民营地,却不欲被人看破——萧彦连乐季也不肯叫跟着,只带了乐孟前往。
游民营地离城墙约莫百步,破破烂烂的帐篷丛里,衣不蔽体的女人大多在奋力浆洗衣衫、缝纳鞋底——替城中居民做活,由小孩进出城门传递,换得半碗吃剩的饭菜。这也是萧彦下令放孩童出入的本意:与其让她们进城分散,倒不如集在一处易得管理,眼下尚未到最难的时候,先保住人饿不死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