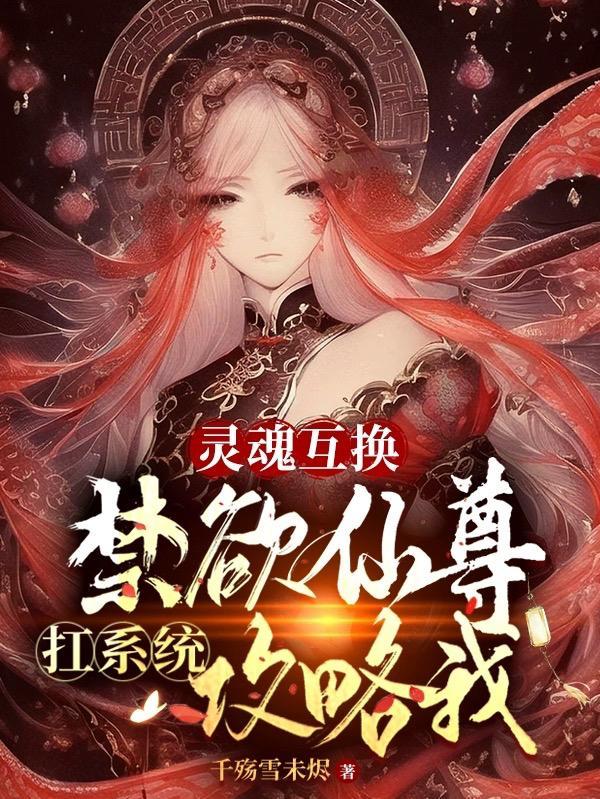少年文学>卿卿误我白玉雪的结局 > 第161章(第1页)
第161章(第1页)
官昱负起双手:“阿姊若是喜欢谢律,自去嫁他就是了,朕不阻拦,他要是来,婚事朕可以答应。”
官卿惊喜交集:“真的么?”
官昱睨她一眼,其实内心当中很是失望,他咬牙道:“阿姊可知当年父王辞世之时,说过一句什么话么?”
这个官卿听过传言,官沧海薨逝之前,拉着床头幼子,曾说“生子当如谢修严”,但官卿以为,那只是传闻!
如今看官昱脸色,似乎并不止如此。
官昱讥笑道:“这句话,始终是朕的心魔。明明朕才是父王的儿子,朕那时候还小,又有哪一处做得不如谢修严呢?父王留下这一句话是何意?朕便偏要让他看看,朕比谢律本事大,朕迟早有一日,将陈国收入囊中,证明自己!”
官卿愕然,怔怔地道:“也许,也许父王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想用这句话激励你,让你有前行的目标,阿弟,你莫想窄了,其实,你聪明优秀,半点不输谢律。”
“是么,”官昱拂袖,笑了笑,“阿姊,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官卿只盼他能应许婚事,不论开出什么条件。
官昱笑道:“你可以与谢律成婚,婚后就依陈国淮安行宫而居,做你的陈国皇后,朕只有一个要求,你要将书杭留下,过继给朕。”
官卿浑身的血液都凉透了,她呆呆地道:“你要书杭?”
为什么是书杭?
四周静谧无声,并无第三人,官昱索性挑明直言:“阿姊,朕有隐疾,生来天阉,生育无能。”
“……”官卿惊讶地看着面前,似笑非笑,明明已经到了发育之年,但其实看着男子特征依然没有显露的弟弟,着实为这个信息震得说不出话来。
官昱对于自己的隐疾,并不愿意多谈,“只要你答应,将书杭留在魏国,过继为朕膝下,朕可以放你去陈国,成全你的鸳鸯梦。”
直至此刻,官卿还无法从这巨大的震惊之中抽回神来,她震惊不已地道:“为何会这样?”
官昱摊手:“生来如此,这就是天命。也许,这才是朕真正一辈子不如谢律的地方,但他的儿子,朕是要定了。”
官卿一直无法消化这个信息,她的脑子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官昱的脸,一会儿是谢律的容颜,一会儿又想到书杭,继而,她想起了三年前,她初来陈国时,那时她被确诊有孕,心神惶惶,不知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儿,也想着官昱根本不可能答应让她留下这个敌国世子的血脉,没想到,官昱答应得很顺利,甚至还一口笃定,让她生下书杭,并跟随着她,从官姓。
事实上,那时孩儿已经认了方既白为父,从母姓的情况在魏国实在少之又少,官昱态度坚决,一定要让书杭姓官,官卿只以为是弟弟体恤自己前半生颠沛流离,将来一定得老有所依。
如今看来,竟是草灰蛇线,伏脉千里。
书杭的这个官姓,本不是为她而保留的,从一开始,这竟就是一场利用的骗局。
“阿弟,你……”
官卿好像突然不认识了这个对自己充满信任,虽然多年不见,但一见面便亲厚无间,甚至依赖和倚重的弟弟,她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难道,这么多年,你一直不放弃各州寻找昭阳公主,是因为,你,只是想,留下一个揣有魏国官氏血脉的孩子……”
这个想法太荒唐,太可怕。
可是除了这,官卿想不到其他答案。
官昱的脸色阴鸷了起来,将脸上全部的稚气掩盖得严丝合缝,不露马脚,他笑着这样告诉官卿:“阿姊不妨往好处多想想,朕想要权势,想要四海一统,想要万古流芳,与朕想要天伦,并没有任何冲突。”
他负手,对这个让他很是失望的皇姊也说了下刀子似的并不好听的实话:“不过,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区区的一个昭阳公主,朕也不至于用雾州和霸州两郡来换。”
官卿几乎趔趄摔倒,以为的姊弟手足之情,原来,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隐瞒、欺骗与利用!
官昱直白地告诉她:“阿姊,昭阳公主的存在,最大的价值便是联姻,若只为联姻,一个真公主,与一个假公主,分别又有什么呢?就算是假的,朕也可以认她为义姊,朕的确在这王位上称孤道寡太久,或许心性有些寂寞,但找回你,实则为了我官家后代,这是朕,绝不可以退让的一步,如若你不肯答应,朕不会准允谢律的求婚。”
末了,他笑吟吟地勾了勾嘴角:“不但如此,朕还会,在魏国杀了谢律。”
官卿懂了。多么讽刺。
她的存在,对于官昱而言,只是一个想要天伦时,召之即来的解闷工具,一个可以说说浅表的心里话的纸篓,一个用来伐陈的名义,一个用来传承官氏血脉的容器!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人,她被他单纯稚气,毫无攻击力的外表所隐瞒和蛊惑,相信他天真无害,深信不疑了整整三年!
“那方既白呢,他是不是也一早就知道,你的计划……”
当年去陈国,用两城换回她,换的到底是昭阳公主,还是为官家生育后代的这具躯壳?
官昱笑吟吟地道:“先生是朕的相父,是朕的左膀右臂,朕做什么决定,怎能瞒得过先生?”
官卿彻底懂了,原来身在局中,可笑的人从头到尾是自己,若再算上别人,便还有谢律。她和他,竟然都是这样被人玩弄棋局间的笨蛋。她以为她比谢律处境好一点,没想到居然是当局者迷,愚蠢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