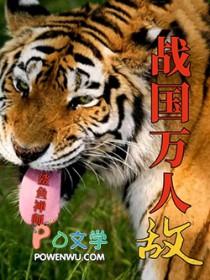少年文学>那个哑巴呀全文免费阅读 > 第65章(第1页)
第65章(第1页)
她仰着头问,小哑巴是谁?
爹刮刮她的鼻子回,他叫陆峥,是个再好不过的孩子。
谭溪月猛然从梦中惊醒,胸脯起起伏伏地急喘着气,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她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她枕着的不是枕头。
昨晚,她用一句睡腻了,把他踹出了她的被窝。现在,她的被子团在床角,她挤到了他的被子里,手紧紧攥着他的手,整个人就跟一个无尾熊一样扒拉在他身上,一条腿还压着他的腿,脚似乎还想往他腿间伸,怎么看怎么都是她睡觉睡到一半,半夜主动摸过来的。
谭溪月慢慢松开他的手,屏住呼吸,悄悄抬起眼,暗自祈祷他千万还在睡着。
四目对上,他正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眼神清明得像是一夜没睡。谭溪月有些尴尬,想把现在这个状况归结到她睡觉不老实上,只是还没开口解释,他直接起身,她顶着他的被子从他身上出溜到了床上,他头也不回地进了洗澡间。谭溪月扯过被子捂住自己的脸,拿脚使劲踢了踢床脚窝着的那团被子,她怎么老做这种打自己脸打得特别快的事儿,她自己都有被子了,干嘛还非要往他被窝里钻。
她在床上装死到他出了卧室,才起来,她用拔凉的水冲了两把脸,脸上的热气才算散了些,一出洗澡间,看到小黑板上的字,用冷水冲得冰冰凉的脸又着起了火。
【我也是个有节操的人
不是谁想睡就能睡
就算你是我媳妇儿
也不能趁我睡着就偷摸地抱我
你这叫耍流氓】
她回到洗澡间,拿抹布将小黑板抹了个干干净净,谁想睡就睡他了,还偷偷摸摸地抱,白给她抱她都不抱。
谭溪月一转身,撞到了一个坚实的胸膛里,她擦黑板擦得太卖力,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了她后面,她身子有些不稳,眼看要倒,顺手抓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贴得更紧。
陆峥没有任何温度的视线扫过她的手,又看向两人贴得严丝合缝的身体,最后轻飘飘地睨她一眼,意思很明显,她又在耍流氓了。
谭溪月松开他的胳膊,后退一步,她不受他的冤枉,“这是你撞到我了,才不是我抱的你。”
陆峥看着她空荡荡的脖颈,屈指弹向她的额头,谭溪月捂着红通通的脑门,抬脚踢向他,陆峥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吃饭】,把粉笔一扔,转身走了,谭溪月想有骨气地说不吃,但她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她红着脸在原地停了几秒,然后捂住又叫唤起来的肚子坦然自若地跟上了他,他都做好了她干嘛不吃,不吃才是傻子。
他做事一向利索,这么会儿功夫都做出了三道菜,清炒小白菜,醋溜土豆丝,清炖豆腐汤,还有白白胖胖的大馒头。
相比往常来说有些素,他每顿饭,早晨肯定会有一个肉菜,晚上至少会有两个,不过不管是素菜还是肉菜,味道都是一样的好,谭溪月把香软的大白面馒头当成了他,嚼得特别使劲,最后就着菜愣是吃完了一个,之前基本半个就饱了,剩下的半个他会解决掉。
饭桌上很安静,她不经意地几次抬头,都碰不上他的视线,车里更安静,她刚从车上下来,他已经拐弯掉头了。
谭溪月站在原地,看着越来越远的车尾,直到车拐了弯,再也看不见,她才收回视线,垂下眼,轻轻踢了踢地上一颗圆滚滚的小石子。
这样也挺好的,一开始说的就是搭伙过日子,他们不该纠缠太深,他有他的路要走,她也有她的路要走。
谭溪月早晨被那一个馒头顶得太饱,心里又装着事儿,到中午了感觉胃里的东西还是满的,也就没去食堂吃饭,晚上回到家,她洗衣服他做饭,闻到厨房里飘出的饭香味,她才觉得有些饿,好在今天开饭很快,她晾好衣服,洗完手,坐上饭桌,愣了一下。
醋溜白菜,煎豆腐,炖土豆。
她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才只是个开始。
一连几天,早晚都是这三样菜来回倒换,她都不知道这三种菜还能有这么多做法,也不是说吃素不好,之前他们家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月能见上一次荤腥就不错了,那会儿吃上个鸡蛋就觉得很满足,只不过这段日子她的胃被他养叼了,天天吃肉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这样乍一停下来,只吃素,哪怕做得再好吃,她也总觉得哪儿少了点儿什么。
食堂里也有肉菜,只不过全靠抢,去晚一会儿就打不到了,而且味道跟他做得都没法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久不见荤腥,一天晚上睡觉,她竟然咬上了他的下巴,她也是奇怪,明明睡觉之前,他俩一人一被窝待得好好的,结果早晨一醒,就又变成她钻到了他的被窝,关键是他冷眉冷眼看她的眼神,都让她觉得她就是活脱脱一个登徒浪子。
钻一次她也就认了,哪儿还能天天钻,她疑心是他半夜把她抱过去的,她想着要装睡逮他一次,只是她都撑不住,最后装睡变成了真睡,她再醒来,又跑进了他的被窝,她的被子是龙凤呈祥,他的被子是鸳鸯戏水,她特意区分过的。
按照他的意思,她天天都在对他耍流氓,她还没地方伸冤去,因为铁证如山的事实摆在那儿,咬他的下巴,更是给这个事实盖了个深深的烙印。
她那天翻冰箱,想自己做个肉菜,咬下巴还好,她就怕自己在睡梦中再抱着他的嘴啃起来,那她真的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结果她发现冰箱里存的肉都不见了,包括她买的牛肉和猪蹄,她想着没准是中秋快到了,他送冯远或者易然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