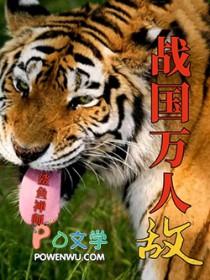少年文学>冬日牛角包的全部 > 第64章(第1页)
第64章(第1页)
谭溪月对上他沉默的眼神,突然觉得有些难过。
那会儿在板面店门口,冯远和易然又把那胖子和瘦子堵了回来,让他们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两个人大概是怕被揍,死活不敢张嘴,谭溪月怕把事情闹大,只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是走路不小心撞到,争了几句嘴,没什么大事情,他确认她真的没有事儿,才挥手让那两个人滚了,她当时能感觉到他看那两个人的目光克制着狠戾。
村里的人只说他以前小小年纪打架有多狠,可要是碰到了跟那两个人一样的烂人,听到了那些烂话,大概只有落下去的拳头才能表达他心里的愤怒,她听到那些话,都会受不了,更何况是他。
谭溪月看着他的眼睛,认真道,“我真的一点儿亏都没吃,我骂他们骂得可狠了,把他们骂得都说不出话来,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这么会骂人。”
陆峥刮刮她的鼻子,一个被惹急了也就只会“王八蛋”“混蛋”来回倒着骂的人,又能骂多狠。
谭溪月直起些身,“你不信?”
陆峥打开灯,侧头看向墙角,谭溪月也看过去,墙角的小黑板上她早晨留下的那又大又粗的【王八蛋x10】直冲冲地进到她的视线里。
谭溪月耳根发红,她一晚上乱七八糟地想了好多事儿,都忘记把小黑板给擦掉了,她用恶狠狠的语气掩饰不自在,“关灯。”
陆峥唇角勾出笑。
谭溪月看到他的笑,人又蔫儿了下来,重新趴回到他身上,陆峥摸上她红透了的耳垂,或轻或重地揉捏着,谭溪月的心也被他揉得忽轻忽重的,她下巴抵到他肩膀上,看他一眼,咕哝道,“骂你跟骂他们能一样吗?”
陆峥怔住。
谭溪月已经扯起被子直接蒙过了自己的头,想从他身上滚下去,但他箍她箍得牢,她根本动不了,动不了她就这样睡,反正被压的是他,他要是不嫌累,她拿他当床垫还挺舒服的。
只是没多一会儿,严严实实的蝉蛹被扯出了一点裂缝,裂缝又一点点变大,她再想方设法地用力抵抗,她用被子砌出的城墙也被人给闯了进来。
被子外面灯光明亮,被子里面漆黑一片,她紧贴着他,连呼吸都绕在一起。
谭溪月要后退,陆峥摁住她的腰,她伸出脚踢他,他用腿夹住她,她张嘴要咬他的肩膀,想到昨晚一些汗水交融的时刻,目光一闪,又没咬下去。
她只能用眼睛发狠瞪他,因为气喘,起伏的柔软一下一下地蹭着他的心脏,滋生出看不见的暗流涌动,带着些许的战栗,清凌凌的眸子荡起恼嗔,她拿拳头砸他一下,“你放开我。”
陆峥依言放开了她。
她往后挪了挪,又挪了挪,两个人还在一个被窝里,她的脚还夹在他的腿间,她想收回来,又有点舍不得他贴在她皮肤上的温度,他腿上的温热从她的脚心蔓延开,连被窝里都被烘出了一种懒洋洋的暖。
谭溪月想到什么,眼神有些暗,舍不得又能怎样,他们长久不了的,他都不一定能陪她走过这个冬天。
她的脚刚一动,他的腿又收紧,她再用力也半点儿都动弹不得。
两人的视线再一次无声交锋,她气急败坏,他稳若泰山,他简直就是把她当成一只傻猫儿来逗。
谭溪月又想咬他了。
陆峥揉揉她快要炸起来的头发,又捏捏她鼓成河豚的脸颊,他执起她的手,问道,【为什么要铺两床被子】
谭溪月一顿,默了半晌,靠近他一些,学着他的样子,胡乱地揉了揉他的头发,捏捏他的脸,手指又慢慢向下,有一下没一下地刮蹭上他的喉结,轻轻重重的,全凭她自己高兴。
陆峥呼吸渐沉,腿间松了钳制,倾身过来要够她。
谭溪月拿抽出来的脚抵住他,冲他嫣嫣然然地一笑,轻声道,“因为我睡腻你了,不想睡了。”
谭溪月用一句话成功地夺回了自己的被子,一个人的被窝虽然总感觉有些透风的凉,但也不是不能忍受,她缩着头躲进被子里,把自己捂成实心的粽子,脑子里回想着今天晚上学过的内容,眼皮渐渐沉下来,进入到了杂乱无章的梦里。
她先是回到了小时候,外面滴滴答答地下着秋雨,爹不用出去做工,娘也不用去地里,她在炕上迷迷糊糊地睡着午觉,娘窝在她旁边一针一线地做冬天的棉袄,她动一下,娘就放下手里的东西轻轻拍上她的背,嘴里还轻声哼着童谣,爹在外屋炖大棒骨,香味一直往她鼻子里飘,哥哥在院子里不知道在玩儿什么,笑得好大声,娘打开窗户压着声音骂他两句,哥哥的笑声小了些,只是没一会儿就又变大了,听着哥哥的笑声,她在香甜的睡梦中也弯起了嘴角。
突然间风雨骤变,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她自己,她被困在浓重的迷雾里,呼啸的风声夹杂着野兽的嚎叫紧紧追在她身后,她胡乱地跑着,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
她想喊爹,刚要张口,却想起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她又想喊娘,可是她不能喊,爹不在了,就该是她来护着娘了,她不能让她再为她担心受怕,她也不能找哥哥,哥哥成家了,他要保护嫂子。
她长大了,是大人了,总要学会靠自己,有些路也只能她自己一个走,她拼命再拼命地往前跑,就在野兽要扑倒她的那一刻,一只有力的手拽住了她,将她从野兽的爪下给拉了出来。
那只手很大,很厚实,又暖和。
她恍恍惚惚中记起,很久很久以前,爹送她到学校门口,温声叮嘱她,要是有臭小子欺负我们小月儿,找不到老师,也找不到哥哥,就去找哥哥班里的那个小哑巴,你跟他说你叫小月儿,他会护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