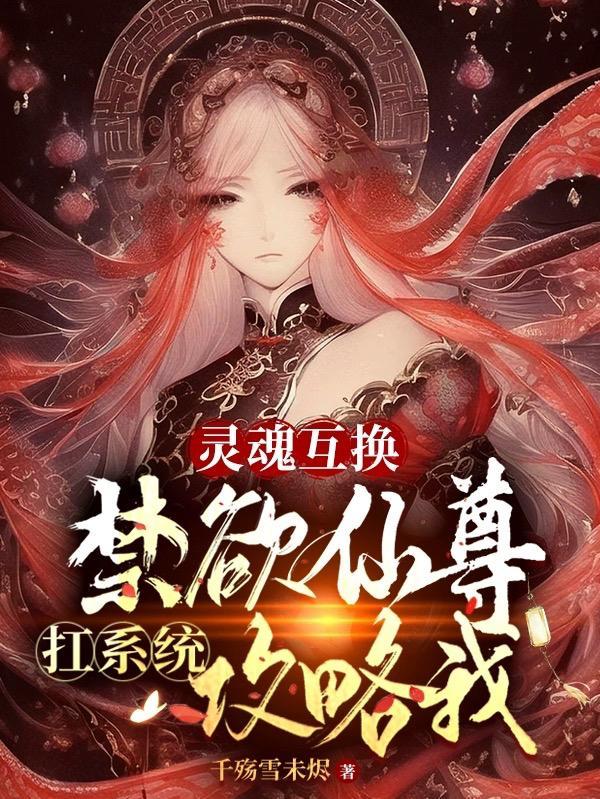少年文学>但成为女帝郗归 > 第79节(第2页)
第79节(第2页)
郗途生于世?家大族,在他的所见所闻中,如谢蕴、郗归这般的女子,自来都?是跟男子一样地上学,一样地读书,她?们的眼界学识,甚至要强过许多男子。
可?在底层社会之中,就连占据了家中绝大多数资源的男人,都?往往没有办法像上层女性那般读书,更遑论女子呢?
困苦的生活不仅会让人抱团,还会催生竞争与挤压。
这些人若能有读书翻身的机会,势必会有意无?意地,首先将这机会捧到同?性跟前。
所谓男女七岁不同?席,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仅不想让女子去?抢夺那本就稀少的机会,还想要剥削女子,压迫女子,将她?们置于社会的沉重规训之中,让她?们不得不陷在繁重的家务里,久久不能脱身,永远不得进步。
这规训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他们想都?不想,便理所当然地按照这规训行事。
可?当郗途拿此?次分田的事情作例子来类比,当这件事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时,这些人便全都?迟疑了。
他们打内心深处感到害怕——如果坚决反对?女子入学之事,郗将军会不会一怒之下,将分给他们的土地统统收走?
周围的百姓们想到这个?可?能,声音不由都?渐渐小了下来,一个?个?小心翼翼地交换着?眼色——反正他们又不是军户,以后会不会成为军户,也还是不确定的事情。再说了,就算真的成了军户,上这蒙学又不要钱,女娃们要去?就去?呗。大不了就是少干点活,反正家中还有妇人们在,倒也累不到自己身上。
对?于周遭百姓们的神色变化,郗途仿佛并未看到。
他始终笑着?,直到这些百姓彻底安静下来,才看向文叟,和气地说道?:“老丈,你这女孩儿很有志气,我们家女郎一定会喜欢。你不如收拾收拾,带着?家眷一道?,随着?我们换防的将士们去?徐州吧。我们女郎是惜才之人,你家既有一手做木工的好本事,一定会过上好日子,这孩子也能有更多的机会。”
文叟嗫嚅着?,没有立时做出决定。
尽管北府军确实如同?传言所说的那般,在三吴谨守纪律,秋毫无?犯,似乎从不欺诈百姓,可?他心中却仍有疑虑——毕竟,一个?女娃娃,就算再有志向,又能有什么机会呢?
郗途并不因文叟的犹豫而感到生气,他瞥了眼喜鹊那双紧紧抓住文叟衣袖的手,宽厚地说道?:“老丈,你且回去?好好想想吧,这事不着?急。”
他虽并不着?急,可?但?喜鹊却显然着?急得很,登时就要扯着?文叟回去?收拾家当。
临走之前,喜鹊看向郗途,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郗女郎不是您的妹妹吗?您为什么也要叫她?女郎?”
郗归虽无?官身,可?却已?经是徐州上下真正的官长,是北府军唯一的首领。
真要论起来,她?如今的身份地位,压根不输上游的桓元,只是没有朝廷的封敕罢了。
“不过,等到三吴之事尘埃落定,台城也该给阿回一个?交待了。”
郗途想到这里,不由爽朗地笑了。
他看向喜鹊,笑着?说道?:“在我们家,谁有本事,便该谁地位高。女郎虽是我的妹妹,可?却是北府军的首领,我作为北府军中的一员,自然要尊敬她?。”
“女子也能做首领吗?”喜鹊听了这话,眼睛蓦地变亮,期待地看向郗途。
旁边一个?男孩笑着?撞了撞她?的胳膊:“郗氏女郎派遣部曲商户,在三吴施了一年的粥和药,你今日才知道?她?是首领吗?”
“不,我只是没有反应过来。”喜鹊瞪他一眼,有些懊恼地驳道?。
毕竟,在郗归之前,并非没有世?族女子施粥施药的先例,只是都?不像郗氏这般频繁,送的东西也远没有这般好罢了。
人人都?知道?,那些贵妇和娘子,之所以会出来露面,与他们这样的贫民停留在一处,泰半都?只是因为要顺着?家中父兄的意思,出来做做样子罢了。
那些粥棚名义?上是由她?们所设,可?却并非纯然出自她?们的意愿。
她?们只是男人们彰显贤德的装点和工具,其善行或是为了给家中男人挣个?好名声,或是为了帮自己抬高身价,以便在议亲时多个?“贤良”的筹码。
喜鹊知道?自己不该这样想揣度他人,行善施德本就是论迹不论心的好事,那些女子总归是帮到了贫苦人家,她?不应这样揣测她?们的动机。
可?她?还是不由自主地觉得她?们可?怜,觉得她?们像一群穿着?锦衣华服的精致木偶,只能顺着?丝线的摆布做事,半点没有自己的主意。
何其可?悲,又何其可?怜?
可?郗氏女郎却不同?。
郗将军说,郗女郎是北府军的首领,他虽是男人,虽是将军,却也要服从于自己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