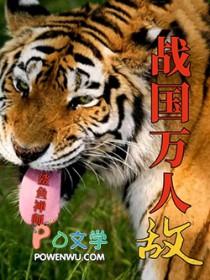少年文学>自甘上流陆雾 > 第78节(第1页)
第78节(第1页)
跪,自是少不得要跪,也不单是他一人跪。避讳一事,上下牵连,有一人遭殃,其同窗至交也一并受累。于情于理,少不得要求情。可求情的折子,太后尽数驳回了,自也无计可施,只得跪求天恩,网开一面。
叶侍郎不是领头的,便跪在后头,瞧着眼前一片朱袍如盖,只暗叹他们着实跪得不够精明仔细,挑了个日头正好的晌午来跪。果不其然,只一个时辰,就昏过去两个,由人抬了送回府上。到底是跪得少了。不比他,仕途坎坷,跪得多了,花样也多。悄悄往影子底下挪了挪,好少些日晒。
待戌时,日落人息,宫里掌灯,有宫人至殿前传口信,道:“诸位大人请现起吧。太后说,大人都是国之栋梁,何必为一些小事伤了身体。明日还要早朝。”
叶侍郎闻言,面上端着不动神色,暗自发笑,想着太后还是老样子,外宽内深的脾气。太监又道:“各位大人请回吧,外面已经备了轿子送诸位回去。叶侍郎请留步,太后有请。”
执事太监在前引路,叶侍郎只低头行路,默不作声。远处又有宫女太监捧蜡烛,传晚膳入各宫。至内廷,太后已静候,奉茶赐座,遣退左右内侍,便道:“叶卿这次回来,似乎又憔悴了许多,路上还顺利吗?”
自是跪下谢恩,道:“承蒙殿下挂念,一切都好。”
太后闻言便笑道:“既然一切都好,叶卿怎么一回来就跪着了?这是谁的意思啊?”
答曰:“殿下之恩德仁义,如春风之沐兮,似日月之曜兮。臣铭感五内,愧不敢忘,偶有所感,涕泪四流。时时自省,便想起昔日疏漏之处,心下忐忑,深恐有负皇恩,便先一步来请罪。”
“阳奉阴违到你这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冷笑一声,她便抄起参他的折子丢过去。折子正打在门面上,人跪着不动,眉心一点红印子,官帽亦是一偏,一缕落发垂落额前。
他亦不做声,只跪地磕头,仰头遥望太后姿容,多年未见,一时恍惚,竟不知今夕何夕。
昔年也有春风得意时,他是少年探花,意气风流。承蒙天家厚爱,受邀入宫赏花,置酒高会。时年太后初掌大权,兴致颇高,便请众人以花为题写诗,他三杯薄酒下头,行事便无所忌惮,只吟道:
“莫怨秋风伤艳色,红梅落做嫁时妆。”
光一句,就犯了两个避讳。一来太后的名字里有个秋字,二来用了寿阳公主的典,难免轻浮。别人是一字之师,他是一字之失。不久便在户部补了个缺,外放去了黄州,自是太后授意。
单是如此,不过是少年轻狂了断前程,书生意气忤逆天恩,说出去倒也是一桩逸事。可坏就在天恩难测。三日后,便有一太监乔装改扮,说有贵人要见他,马车载他到一处僻静小院。他一望地上的车辙印,便知前一辆是宫里来的。这一趟是不该来的,可退也退不得来,索性大大方方便进去。也无人引路,过两道门,至内院,他定了定,到底也慌,不知该不该进去。
有一女子在房内道:“你不敢进来?”其声清脆,然威不可测。赏花宴上听她说过话,他认得她声音,自也为难,道:“再走一步就是死罪了。”
她反道:“你现在也是死罪。”
他便道:“好在我只有一颗脑袋,到底只能被砍一次。”
里间一阵静,须臾,竟听她笑道:“朝廷礼遇读书人,哪有当街问斩的道理?你放心好了,拖你到无人处杖责,至少能打个三四次不断气。”
左右便不过一死。他低头,大跨步入内,见房内一珠帘隔断,隐约可见太后身影,做寻常妇人打扮,只佩一珠钗,然其容貌娇丽,自不必由金玉衬托。
因他一时又不敢近前,显出少年青涩态。她便笑道:“之间见过了,怎么还看个不停。”答曰:“先是跪着,然后低着头,没看仔细。”
珠帘挑起,嫣然含笑,又道:“那我和你想的一样吗?”只得如实答道:“比我想的小很多。”掐指一算,皇帝才两岁,太后不过廿二,听说是十五岁入的宫,二十岁当的皇后。
虽读的是圣贤书,但也只知怜我怜卿。他只大着胆子脱靴就寝,与她双手交握,又忍不住一缩。她由此调笑道:“都到了这地步,还怕什么?”
“不是怕,你的手太冰。”
当真是君非君,臣非臣了,颠鸾倒凤是倒,七颠八倒也是倒。一阵珠帘摇曳,乌发相织。事毕,他服侍她起身更衣,又帮着挽发,似是民间少年夫妻。到底不是精于此道,他只把她的衣带胡乱系上,自觉不妥,便道:“怎么也没人伺候着。”
“要是有人伺候着,他们还能活?”
“那我能活?”他把茶杯端到她面前,凑着她的嘴喂,一样洒出来些。她笑着斥道:“笨手笨脚的。”
之后数载宦海沉浮,自也身不由己。因他为人正直,性情豁达,治水有功,几番升迁,又爱提携后辈,恩名远播,一时倒也成了南方文臣中举足轻重之辈。只可惜东安王一事,他带头上书,惹了太后忌讳,又连遭贬谪。
赴任途中染了病,没到驿站就开始咳血。一路拖延到府,才找了大夫看诊。先一个称是喘病,不打紧,可要仔细养着,不然容易留病根。三四个月里不能碰凉物,不能洗澡。
五黄六月,他本就拿湿帕子搭着面,惊得从床上坐起,道:“三个月不洗澡?我必不是这病。”一连说了两次,急急遣仆从把人打发走了。
又去叫人,后一个大夫说是心漏,又问可否沐浴更衣。答曰:“凡事都不忌讳了,心漏是胎里带出来的病,药石无医,到了咳血的时候,也就一两个月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