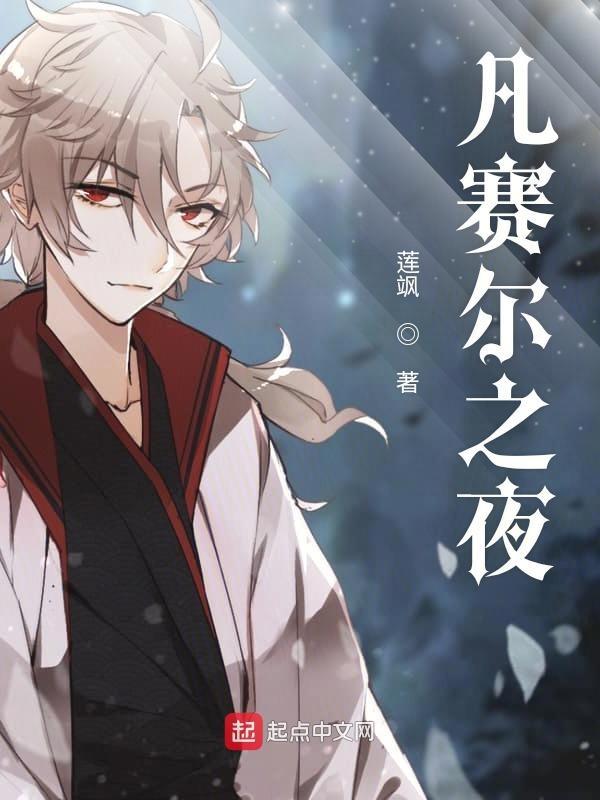少年文学>青梅她好甜免费阅读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驸马曾有过婚约?”她直白问出疑惑,陆清如顿了顿。
“听瑜儿父亲提过,但只是两家父母玩笑话,且八字不合,做不得数。”
陆清如心中怪怨陆渊提及旧事,那位周家的小姑娘杳无音信,或许已不在人世。她虽没见过那位,但听徐崇礼话里的意思,周姑娘自幼便蛮横不讲理,最爱追着徐从绎撒泼,说好听点是欢喜冤家,不好听是死对头,是宿敌。
她有意岔开话题,拉着裴炜萤进她的卧房,神神秘秘关上门。
她是河东有名的才女,徐崇礼过世后便搬回白鹤书院,招收女学生。
她捧出一个匣子,递到裴炜萤手里,笑道:“宫里的嬷嬷应当教过公主,我也不多说,但天底下没有比我这更精美详细的,保证公主看了大有益处。”
裴炜萤已经猜到是什么,烫手山芋一般不想接,陆清如看似循规蹈矩,反而很豁达开明,“公主别怪我逾越,绎之和你的婚事是皇命难违,但日子靠你们经营,你抓牢他的心将来也不必夹在中间为难。”
徐令仪孩子都有了,郭岐也并未因此妥协。
裴炜萤没那么大的远见,离宫前皇后是暗示过她,但朝廷若无力征伐北燕,却觊觎三镇兵权,害得人人自危,只会祸起萧墙,重蹈前朝覆辙。
如今河东与范阳看似交好,可徐从绎不见得忍气吞声,纵容郭岐一再辜负徐令仪,羞辱徐家门楣。
他若能将河东与范阳收入囊中,占尽大齐三分之一兵力,还甘心屈居为臣,受朝廷桎梏吗?
河东与京城只隔着一道黄河,攻与不攻,只在他一念之间。
现在三镇各怀鬼胎,彼此制衡,反倒是最好的局面。
她来河东,可不是为了挑起宏大重任,尽到应尽的责任就好。只等季临一封信,她便可正大光明回她的封地,采矿烧瓷,抽空和徐从绎睡上一觉,维持淡薄的夫妻情分。
见她犹豫,陆清如塞给丹朱,千叮咛万嘱咐:“给你们公主的好东西,千万收好。”
裴炜萤只好点头,学点东西总没有坏处。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裴炜萤再拉不下脸当着来来往往的人被徐从绎抱下山,幸好山上备有轿撵,她总算安然无恙回到马车上。
回程时徐从绎去往原州府衙,她的公主府还没着落,但整个徐府只有她一位主子,很是清净安逸。
她足不出户歇息一天,起身问丹朱收没收到季临的信。
原州到黛县快马一日可达,季临知她性子急躁,应落地就发信给她了。
又空等一日,裴炜萤待不住,卷起披帛吩咐鹤云随身,带着雪青和丹朱前往原州府衙。
原州府衙书斋外青松百丈高,孤高盘踞小院,挡烈风遮烈日,四季不落。
斋内窗明几净,正中一方楠木书桌,两侧竹榻茶垆,壁上白鹤图。
徐从绎一袭群青圆领窄袖长袍,银冠束发,腰间雷打不动一块青龙玉佩,他举着狼毫斟酌下笔,书写罢放在一旁晾干,这才拆开堆了两天的信件,面无波澜投入垆中焚烧,很快化作一缕青烟。
府衙的门房眼瞅着气派豪华的马车停在门口,里面伸出一双嫩笋般的手,走出娇花般的人,只是侍女便看痴了他,他已猜到来者身份,忙跑去通风报信。
“公主来了。”
一路喊到书斋,徐从绎已经从容收拾好书桌,提起茶壶倒一杯热茶,静候芳驾。
裴炜萤娉婷而至,珊瑚色如意纹齐胸襦裙衬得肤白如雪,沐在日光下莹润耀眼,玲珑可爱的耳垂上的翡翠坠子晃晃悠悠,直摇进人心里。
粉腮玉肌,婉婉生香,白天是牡丹芳菲,夜间是清辉月影。
她轻提裙摆,越过门槛,一缕幽风似的径自在竹榻坐下,身后的雪青丹朱各提漆盒,取出饭菜一一摆开。
鹤云严阵以待,守在门口。
徐从绎看了她两眼,虽没寻到蛛丝马迹,心中仍道今日鸿门宴,来者不善。
他先谢过:“殿下有心。”
裴炜萤一笑:“我初来乍到,不知驸马在府衙吃得可好,睡得可好,横竖眨眼可到,便自作主张登门探望。”
徐从绎摸清她的脾气,唤他驸马、夫君时她必定心有讥讽和算计,唯独“你”呀“我”呀才是和他推心置腹,真情流露。
“有劳殿下,臣在府衙一切安好。原定明日休沐回府,这些时日委屈公主独守空房。”
裴炜萤禁不住他调弄,面颊粉粉,脱口问道:“什么独守空房?”
徐从绎目光瞥向食盒里,赫然一道鱼丸汤羹。
裴炜萤显然不知情,芙蓉粉面腾然烧红,抿起朱唇斜他一眼。他岂肯放过逗弄她的机会,悠然坐下拉她的手,扣住腰身揽明月入怀。
裙摆堆在腰间,裴炜萤与他拥吻片刻,脊背袭来一阵凉风,挣扎要从他身上下来,指了指大开的房门和窗。徐从绎索性抱起她往里走,关上内室的门,放在他夜间就寝的红木雕花床上,俯身压下来。
“我不是来和你行事的。”裴炜萤推他的胸膛,可又说不出所以然,思索的功夫已他已褪下襦裙。
粉白盈盈绽放,莹玉肌香,皎皎姝色,灼灼芳华,百般娇美。
“来都来了。”
徐从绎再不想听她东拉西扯,吻她口脂甜蜜的唇,似在她口中尝尽百花的香甜,一双手已游刃有余,贴上她沁凉娇软的肌肤,肆意撩拨。
她闭上眼睛,被他勾得巧笑嫣然,浑身火烧火燎,身子早软成水,伸进他衣襟胡乱扯开,不甘示弱抚弄。在他弓紧身子操办正事时她攀在他肩膀上喘息,抓他的宽阔的背保持清醒,这才得以看清屋内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