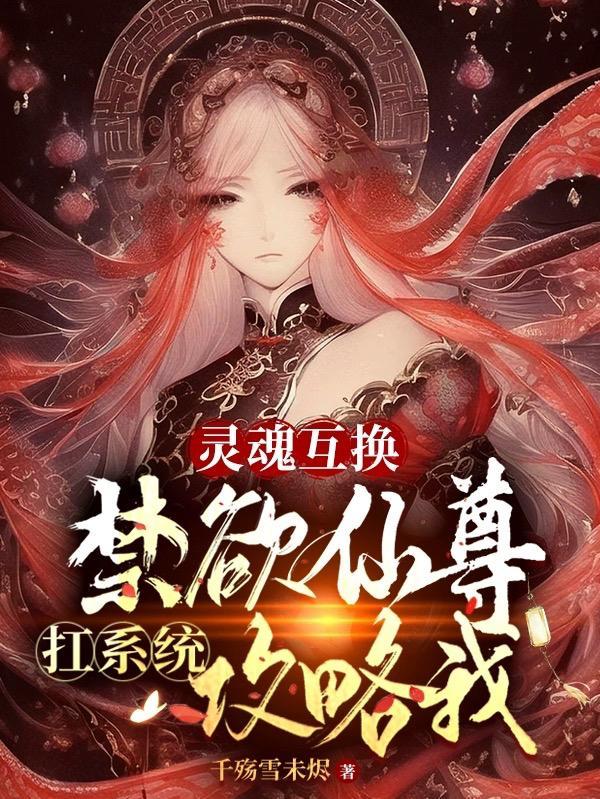少年文学>首辅重生后夫人丢了结局 > 第23章 发了高烧(第1页)
第23章 发了高烧(第1页)
崔元卿将水杯往桌上一掼,走出房门,不一会儿领了海棠和牡丹过来。
程颂安看了眼桌上的自鸣钟,急道:“时间差不多了,你快去。”
海棠道:“缎子送的迟一些有什么相干?你身子这样,我怎么放心去?”
程颂安指着那匹蜀绣,干哑的嗓子几乎有些破音:“叫你去,你便去,家里有牡丹她们呢。”
崔元卿皱了皱眉,淡声道:“主子安排的事,利落去办,推推搡搡地做什么,哪里就娇贵死她了?当我也是死人吗?”
程颂安听了重重将拳头捶在枕上,恨声道:“我的丫头再不成,自有我教训,你不许说她!”
她今年已有十八岁,脸上早褪去了稚气,出落的大大方方,然在病中,脸带潮红,又生气,腮帮子有些鼓了出来,言辞虽利害,却让人觉得好笑。俨然又是十多年前,娇纵霸道的益州孩童中的一霸。
崔元卿心中一动,不跟病中的她计较,只眼神凌厉地看了一眼海棠。
海棠顿时低下头去,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抱起桌上的那匹蜀绣走了出去。
崔元卿有些意外地看了眼,她病成这样,牵挂的竟是这块料子?是要裁衣服?他现在并不缺换洗的新衣。
他不自然地转了目光,朝牡丹道:“将午饭端进来吃。”
牡丹连忙过去,端着一张小几,上头只摆着几碟清淡的佐菜和清粥。
程颂安看了,苦着脸摇摇头:“我不爱吃这些。”
崔元卿冷冷道:“由不得你挑食,病着就要有个病人的样子!”
程颂安烦躁地抬眼瞪他:“你一直在这里做什么?”
崔元卿:“你以为我愿意么?若不是祖母硬逼着,我才懒得管你。”
程颂安冷哼了一声,怪不得他还喂她喝水,原来都是祖母逼的,恐怕心里已经骂了她千百遍了。
她嗓子不好受,被牡丹喂了些粥,肚子隐约有了些暖意,便不再吃了,又重新躺下睡觉。
只是这一觉睡得绵远悠长,梦中前世今生不断交错出现,让她分不清身在何处。最后画面依旧停留在后来的筠香馆,只剩下海棠伴着她,毫无希望地等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身子逐渐烫起来,全身每一处血肉都疼的厉害。她抱着被子,身体开始颤。
忽然,整个人一轻,像是被人拽了起来。
崔元卿一脸怒容抓着她道:“程颂安,你别说又喝了药膳!”
程颂安烧的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了,没了被子的遮盖,寒意侵来,让她只觉得骨头缝里都泛着酸楚,痛到身体打摆子。
她瞪着空洞的大眼,漫无目的地找寻着,声音颤:“海棠呢?海棠,别离开我!”
声音又干又哑,说不出的凄惨。
崔元卿一愣,松开了手。
程颂安直直摔在床上,她胡乱地抓着,没抓到什么,仰着脸瑟瑟抖:“我又要死了,海棠,我只有你了,别离开我,我害怕……”
崔元卿扶着她的肩膀,将她对着自己的脸,皱眉道:“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程颂安对上他的眼睛,猛地瑟缩了一下,崔元卿的脸在她眼前不断放大,那些厌恶的表情无比清晰。
她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崔元卿,我跟你和离,你放我走吧,不必等我死,我将这个位置让给她。”
崔元卿抓着她肩膀的手骤然紧了紧,低声道:“程颂安,你就这么想跟我和离?”
程颂安本就痛不欲生的身体,更痛得如要一片片裂开,她挣扎着:“我死了一次,不欠你什么了,你别把海棠也赶走。”
崔元卿看她涨红的脸颊,手中的触感滚烫如沸,才明白过来,她了高烧,烧的开始说胡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