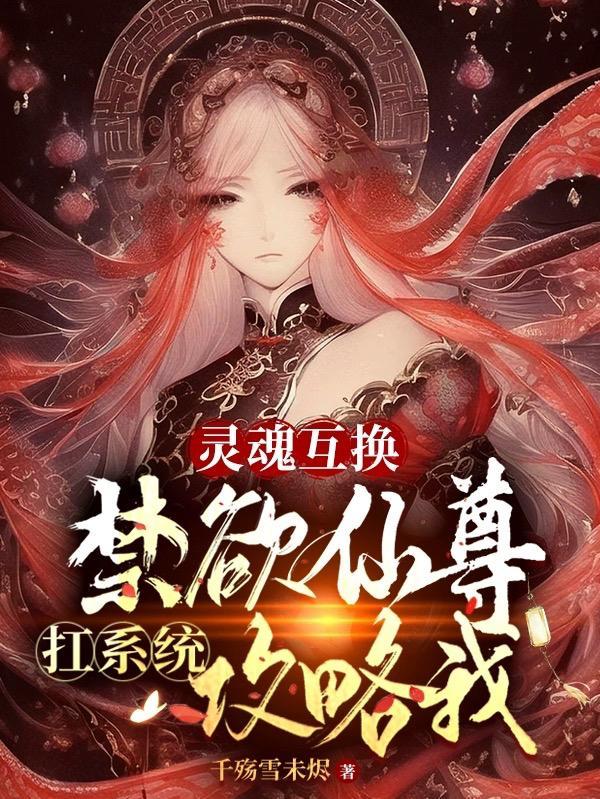少年文学>非练实不食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郑来仪笑了笑,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小时候自己便对马感兴趣,五岁第一次缠着父亲带自己骑马,那马儿似乎是感知到马背上多了个人,存心要把她颠下来,等到郑远持费力控住马,小娃儿已经吓得不成样子,还尿湿了裤子。
后来自己便对骑马始终怀着复杂的情感,又想骑,又害怕被马欺负。
真正手把手教她驭马之术的人,还是……他。
她面上的笑容蓦然冷了下来。
冷不丁想起那个人,郑来仪如同被厚重的黑雾罩住,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她咬紧了牙,狠力一夹马腹,胯-下的马儿陡然受到刺激,便如离弦的箭冲了出去。
“哎!椒椒!这马尚未完全调教好,要小心啊——!”
李德音的话音还未落地,前面的人已经冲得没了影,他无可奈何,只好狠甩了一下马鞭,纵马追了上去。
黑马疾驰如电,带着郑来仪迅速穿过了半个牧场,黑色的鬃毛在风中飞扬,拂过郑来仪的前襟,飞速的奔跑似乎带起一阵最为猛烈的飓风,吹得郑来仪睁不开眼,然而这样的速度却让她感到畅快不少,方才因为想到那人的窒息感都被冲散了。
“椒椒……等、等等我……别跑那么快啊啊——很危险啊!”
身后传来李德音气喘吁吁的声音,郑来仪头也未回,抬起右臂又是一鞭。
身后追赶的人是来日的太子,甚至可能是皇帝,她却顽劣心起,想着未来的帝王就这么龇牙咧嘴地一路狂追,有种荒谬的滑稽。
李德音看不见郑来仪面上突然的笑意,只能无力地望着黑马载着那盈盈一握的倩影愈去愈远。
这么没命的跑着,不去想到底要去哪里,一时的自由和空茫,似乎是郑来仪重返人世以来最简单纯粹的一刻。
她跑到听不见李德音过分殷勤的声音了,前方连绵的山脉也离自己越来越近,方才准备降下速来,勒缰调转马头。
回头时才发现,的确是跑得有些远了,而这匹乌霜似乎也是跑得十分畅快,被勒住回头时还显得有些抗拒,似乎是不愿就这么回去。
郑来仪俯下身子,拍了拍马头,“这么无拘无束地跑起来,的确很痛快,对吧?”
马儿喷出一口气,左右摇晃着脑袋,似在附和她。
于是她直起身体,朝着回程的方向甩起了鞭子,纵容的语气:“那就再跑一会儿吧!”
这一回,马儿似乎比方才还要兴奋,四蹄欢快地甩动着,马背上的人起初随之上下颠簸,感受着马儿的激动,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没有一会,郑来仪突然变了脸色——自己的脚似乎被马镫卡住了。
从学着骑马的第一天起,郑来仪就被教过,脚要踩稳马镫,但切忌被卡住。她也亲眼见过战场上一只脚卡在马镫里松脱不得,被马儿拖行十几里,被活活拖死的成年壮汉。
一手攥紧了缰绳,郑来仪低头一看,背后瞬间起了冷汗——鹿皮短靴上的流苏不知何时缠在了马镫的铁环上,看样子缠得还很紧。
她心中方寸大乱,一时间甚至听不见耳边的风声,只有沉重而不断加速的心跳,一下下振动着自己的耳膜。慌乱中环顾四周,视线尽头似乎能隐约看见白色的尖顶。是营房。应当离他们出发的马场不远了。
她下意识绷紧了身体,微微扯了一下缰绳。
马儿于放肆奔跑中接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指令,如同不肯听话回家的孩童,更激烈地跃动,想要摆脱束缚,郑来仪心中的慌乱尚未平复,僵硬的身体信号被黑马敏锐地感知了。
她与它的磨合尚不到半个时辰,就好像势均力敌的对手将将能打个平手时,突然露了怯。马儿的顽劣愈发有恃无恐,加速奔跑的同时大幅甩起两只后蹄,郑来仪几乎握不住缰绳,有一瞬甚至从马背上腾空而起。
她紧攥缰绳的手已经湿透,全身的力气都用来让自己不被马甩飞出去,甚至没能听见旁边有人的惊呼声。
李德音远远看见重新出现在视线中的人,尚未来得及欢喜地迎上去,就察觉出不对:郑来仪驾驭的那匹黑马简直如同疯了一般。
“椒椒!你抓紧啊、千万抓紧!!我、我——我来救你!!!”
饶是嘴上这么说,可李德音根本无法靠近她,他坐在马上束手无策,只在原地来回踱步。
就在这当口,那匹失控的黑马已经载着郑来仪从他身边穿梭了三个来回,逼得他不得不避让。
郑来仪面色惨白,脑中的理智全然被濒死的恐惧冲散了,有那么一瞬,她几乎想放开手,屈服于这难驯的马儿,却在快要力竭之际,余光瞥见马场边静静站着的一个人影。
心跳仿佛一瞬间静止。
叔山梧抱臂站着,沉眉望着场中,一霎视线与她接入了同一个轨道。
男人掌心的温度隔着仿若无物的布料熨至肌肤
叔山梧的眼神落在郑来仪的马上——这匹乌霜自幼马时便被他亲手选中,此马性格高傲刚烈,经过几个驯马师都未能将它完全驯服。
他皱了眉,他们居然让她骑这一匹马,还是驏骑,不知是马场上的人不懂轻重,还是这郑四小姐胆子太大。
叔山梧冰冷的眼神如同一剂猛药,将郑来仪的求生意志唤醒——她好不容易才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若真在他的面前被马拖死,实在是太冤了!
“椒椒!!你别急啊……椒椒……我、我来了——!!”
那边厢李德音已经翻身下了马,几度想要朝着郑来仪的方向跑过来,都被黑马的癫狂之势无奈吓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