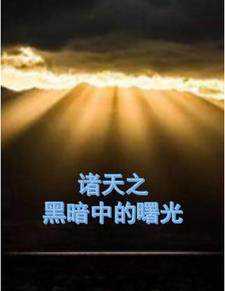少年文学>风止何安什么意思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纪时愿注意力一下子被转移走,对着玻璃照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委屈巴巴地控诉:“秦姨说我既然住在她家了,就得付房租,但她又不要钱,非要让我包饺子给她吃……二哥,你也知道我这辈子就没下过厨房,这简直和要我的命没什么两样。”
纪浔也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那你继续,没包好就别出来了。”
纪时愿想打人的心都有了,眼珠子一转,把主意打到叶芷安身上,忙上前将人拽到厨房,“妹妹,你来帮帮我。”
叶芷安毫不扭捏,爽快应了声“好呀”,揉面粉前先去洗了手。
窗户半边开着,橙黄的光束投射进来,和屋里的冷白灯光交织在一起,把人的脸都照得有些晨昏难辨了。
叶芷安视线微垂,落在她们沾满面粉的双手上。
和她不一样,纪时愿拥有一双养尊处优的手。她的呢,看着柔软,捏起来却不那么细腻,甚至称得上有些粗糙。
憋了五分钟,纪时愿终于憋不住了,开始八卦:“你和我二哥什么时候认识的?”
叶芷安在“四年前”和“一个多月前”两个回答中选择后者。
“酒吧不是第一面?”
“我是在蓦山溪见到他的。”
纪时愿明显对那三个字印象不佳,但也没问她怎么去了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只感慨道:“那我哥算是对你一见钟情欸。”
一见钟情?
叶芷安听了想笑,她和纪浔也交换还差不多。
纪时愿兀自摇头称奇,再次开口时声音轻了不少,“这倒是头一遭。”
“嗯?”叶芷安没听清,想让她重复一遍。
纪时愿停下手上的动作,眼神认真了些,“我告诉你哦,我二哥活到这岁数,身边都没有过人,不过这也不能代表他和这几年网上的流行的说法一样,是个纯爱战士,相反他满肚子坏水,典型的商人嘴脸,从来不做没有回报、或者产出小于投入的事。用一句话概括他这个人,就是看似深情,实则无心。”
纪公子的毛病三天三夜也数落不完,最混账的那段时间,狠起来拳拳到肉,疯起来又兵不血刃。
论起狠起来折磨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前一秒他能笑着配合你称兄道弟,下一秒就能踩断你的髌骨,逼迫你昂着下巴对他俯首称臣,谄媚的笑让他不满意,鼻梁多半也会留不住。
他这人还爱清静,真正动起手教训人时,会先往人嘴里塞上棉布,不紧不慢地道声:“听话,咬住这玩意儿,一会儿就不会疼到喊出声了。”
另外,鲜少有人知道,李家兄弟现在最爱在淮山玩的“撞人”游戏,就是纪浔也开的头。
起因还和她有点关系。
高二转学后的第一学期,她被高年级的几个校霸盯上,受了些委屈,回家第一时间找纪浔也哭诉。
隔天晚上,那几人就被绑到淮山,整整齐齐地跪坐一排。
纪浔也坐在车里,踩下油门,引擎声的轰鸣将那几颗心脏高高甩起,摔了个稀巴烂,□□的尿骚味引得其他看热闹的人哄堂大笑。
车头最终停在距离他们不到半米的位置,那几人除了脸面尽失外,毫发无伤。
纪时愿心里很清楚,纪浔也这种报复手段不见得有多想替她出气,满足自己的顽劣心才是目的。
换句话说他的行事全凭喜好,没几个人真正被他放在眼里过。
说得再矫情点,偌大的北城里,爱他的人和恨他的人一样多。
所以别指望他能在一段感情里投入多少真心,挥洒真金白银的放浪生活才最合乎他的精神需求。
叶芷安低垂着眼,嗯了声。
给出的反应实在简洁,纪时愿一时半会都分不清她已经开始替自己的命运黯然神伤,还是完全不在意旁人眼中的纪公子究竟是什么样。
“我说这话不是在劝退你,也不是在挑拨离间,我只是希望你能想明白,和他短暂地在一起,又或者就此离他远远的,哪个会更让你后悔、遗憾。”
叶芷安还没来得及给出回答,纪浔也含笑的眉眼撞进视线,问她们在聊些什么。
纪时愿撇撇嘴,“女孩子的秘密,你一个大男人少打听。”
纪浔也睨她一眼,又看向叶芷安,见人心事重重的模样,语调不由沉下来,藏着几分警告,“聊秘密是可以,但别扯不该扯的事。”
接下来的话,其实更像是想让叶芷安听到的:“安分点,别去惹这小祖宗生气,不然又得我去哄。”
叶芷安听了只觉荒唐,想狠狠控诉一番,却在对面似笑非笑的目光中缴械投降,小声嘟囔:“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样这么对祖宗,家家户户十八代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纪浔也唇角弧度挑得更大了,扯扯她的脸,“是不是又在偷偷埋汰我?”
叶芷安当然不会承认。
在被纪浔也叫出来前,叶芷安已经吃过晚饭,但架不住秦之微的热情,又往肚子里塞下几个水饺。
饭后,纪浔也无视秦之微警告的眼神,带叶芷安去了夜市,纪时愿来梦溪镇后就没好好逛过,好奇心作祟,充当了回自己一向不齿的电灯泡角色,屁颠屁颠也跟去了。
梦溪镇的花灯节从除夕开始,到元宵才结束,正因为是第一天,人流密集,叶芷安差点和他们走散,纪浔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找人上,直接攥紧她的手。
叶芷安挣脱不出来,也舍不得挣脱,由着他去了。
四十分钟后,写有他们祝愿的花灯在朝露河上飘荡。
纪时愿不忘双手合十,虔诚祷告,“我希望沈确那魔鬼一觉醒来,能变成傻子,再不济,失个忆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