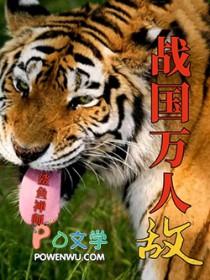少年文学>司机与少爷by怪盗红斗篷 > 第21章(第1页)
第21章(第1页)
打开电视机看看新闻,上头播报什麽什麽党又骂什麽什麽党,哪个预算案有问题,陈大树有看没有懂,更加低潮了。
特别是新闻最爱播报失业率,人民有多痛苦,多少人因为没钱而起歹念,陈大树看得心有戚戚焉,他现在也是失业人口了,虽然他将会有一笔数字可观的遣散费。
陈大树觉得真痛苦,他现在做什麽都难过得想大哭一场。
他到底是因为失业而难过,还是因为失恋而难受──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他没少爷那麽绝决,少爷本来就是个残忍的人,虽然在他面前总有孩子气的时候。
陈大树意识到自己陷得有点深,以至於现在无法自拔的地步。
他很想见少爷一面,想知道他最近过得好吗?他们从没分开这麽久过,少爷总会想各种藉口,让他上山去接他。
陈大树在家里不知道要做什麽,乾脆打扫房子,好好地大扫除一番。
陈杰弘买饭回家,发现家里被彻底打扫过了,一脸不可思议。
「哥,你干嘛?」
「我?我在打扫。」
「你是伤患,应该要躺在床上好好养伤!」
「我静不下来,不想躺著……想起来活动活动。」陈大树反驳。虽然说他确实做大动作的时候,扯到伤口会很痛,所以他尽量用小幅的动作去做。
陈杰弘将粥放到桌上,催促他哥放下拖把过来吃饭。医生特地交代,他哥现在只能吃些流质的食物。陈大树坚持拖完最後一区块,才去餐桌。
陈大树坐下来,叹了口气,「我大概是劳碌命。」
「别这麽说,你只是还不习惯退休生活。」陈杰弘劝他。
「我跟你没差几岁,你都还没工作,我就退休了,这像话吗!」陈大树皱眉,叨念著,又起身,去给两人倒杯果汁。
陈杰弘看他哥没一刻停下来,觉得心酸,以前都没发觉,大哥一提,害他也意识到了。他大哥搞不好真是劳碌命也说不定。
「你就当做放暑假,在家好好静养两个月。我们现在又不缺钱,再说,你不是还有遣散费可以拿,不用那麽急著找事做。」陈杰弘苦劝他,「吃饭吧,你要拿什麽跟我说,我帮你用就好。」
陈大树安静下来,乖乖吃饭。
陈杰弘打开电视,没什麽节目,看看欧美电影,随意地看。
电视正在拨放植物杀人的电影,陈大树看得挺起劲的,饭後也继续看,直到整部片做完。陈大树知道自己要做什麽了,他想买一台dvd拨放器,然後借一堆电影来看,把他这几年来没来得看就下档的电影补完。
一旦决定,立刻行动,陈家两兄弟出门买器材,买完器材,去租片子来看。
「为了一个念头就买这麽多东西,总有一种消费的罪恶感。」陈大树说道,这跟为了弟弟妹妹学业而买电脑花大钱的感觉不一样,这东西是他自己想要才买的。
陈杰弘听了有点难过,他哥就是太为他们著想,事事都想著他们,所以没为自己花过什麽大钱。辛苦赚钱也是为了他们,还要委屈自己。
「弟?你脸色突然很差,是不是不舒服?」
「没有。你才是,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陈大树摇头,又迟疑一会,四处张望。
「怎麽了?」
「没、没什麽。」陈大树否认。他察觉到一股视线感,跟在饭店的那种危机感不同,对方似乎只是看著他而已。那种感觉有点熟悉,像是被袁家保镳看守时候那样。
袁家派保镳来保护他?可能吗?他都被开除了。
「是我神经敏感了。」他想。
「嗯?」
「我们走吧。」陈大树催促他,戴好安全帽,坐上陈杰弘的机车。
陈杰弘负责骑车,陈大树回头探望,寻找视线源头,什麽也没找到。
会不会是枪击过後的後遗症?确实他面对玻璃窗的时候,会莫名地赶到毛骨悚然,所以他尽量靠墙走。或许视线感也是後遗症的其中之一。
在过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陈大树又回头一次,他的眼角馀光好像瞄到袁家的保镳车,但只是类似的车种,没看到车牌他也不能确定,保镳车种是最一般常见的车,大隐隐於市。
他大概是太想见袁哲林了,居然出现这种幻影。
袁哲林不接手机,也不联系他,还透过管家来辞退他。从出事到现在,他一眼都没瞧见少爷,对方也不来来探病。真够绝情的。
好像前一刻他们还在车上讨论趁堵车之际抓准时间玩口交,突然之间,就变成两条平行线,毫无交集的两个人了。
如果他能再见到袁哲林,他肯定要狠狠痛扁他、教训他一顿。告诉他,他可是帮他挡了好几枪,再怎麽说他也应该要见他一面。至少──至少让他亲眼确定他是真的平安无事了。
陈大树心里明白,他不可能有这机会了。
作家的话:
☆、司机与少爷22
袁家当家风光下葬,新闻连播好几天的报导,作为接班的袁哲林不免被镜头捕捉,关於记者的问话他一个都不回答,交由发言人负责统一回应。
陈大树终於见到他的少爷,在他们一家三口吃晚饭的时候,袁哲林毫无预警地出现在电视上,仅仅几秒钟的匆匆镜头。三个人自有默契,沉默不语,安静吃饭。
陈大树心情异常平静,那个人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新闻很快播报下一则新闻,又是哪个歹徒持刀抢劫超商。
陈大树吃完饭,收拾自己碗筷,又走到电视机前,询问,「你们还看新闻吗?不看的话,我想继续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