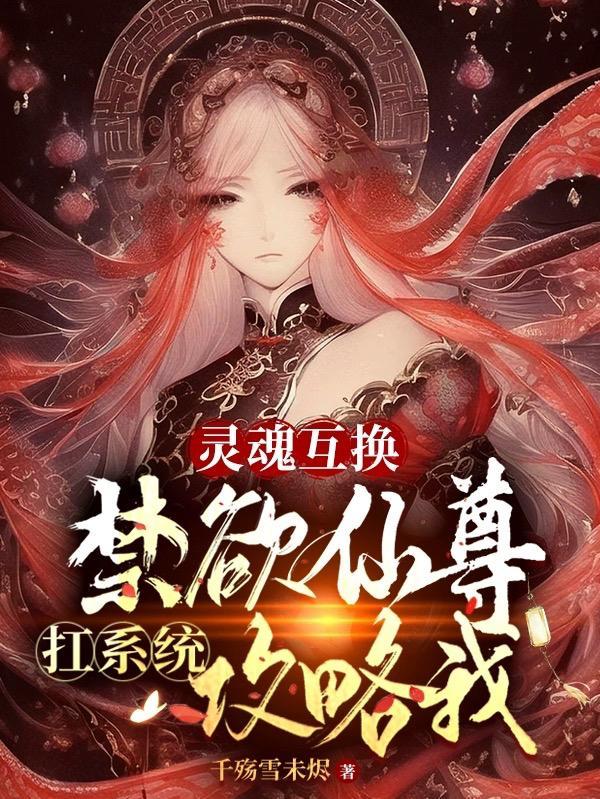少年文学>太子妃今天也想篡位gb28 > 第227章(第1页)
第227章(第1页)
殷明垠在刀剑厮杀声中惊醒,他纠缠在凌乱的衣袍中,临产的腹部高耸,修长玉颈遍布冷汗,孱弱挺起腰腹,指尖痛苦地拧紧了衣袍。
他此刻阵痛激烈,宫缩不断将孩子往下推挤,硕大的胎头已经撑开他的盆骨,进入产道,连双腿都合不上,遑论逃跑。
他在惊惧中颤巍巍仰起头,倒悬的视野里,看见车窗外涌动的人头,一张张狰狞的脸孔正拼命往里钻,雪亮的刀尖刺穿帘幔,向他捅来,又被马车外的人惊险制止。
殷明垠胸膛起伏,挺着肚子动弹不能,惨白的指尖攥紧了衣袍,试图护住腹中孩子。他眉眼皆是冷汗,精巧的喉结滑动,颈间扯出经络,在惊惧的刺激下溢出激痛的呻吟。
温热的潮湿感骤然突破,殷明垠眉眼汗湿,咬唇轻哼,感觉自己失禁一般,有液体顺着双腿流下来,衣袍下摆很快被浸湿。
“瑗儿……!”
破水后更激烈t的剧痛碾磨他狭窄的盆骨,殷明垠的瞳孔涣散又收紧,像缺氧的鱼恹恹喘息,无助地向车外张望。
他不知车外发生了什么,却知状况前所未有的危急,顾西瑗可能已经遭遇不测的巨大恐惧像黑洞吞噬了他。
马车周围的中原士兵一个接一个倒下,只剩弘遂一个还在硬撑。双方的尸体堆积在马车边,更多的北狄兵踩踏着尸体爬上来,推挤着马车,刀剑从车顶、车窗所有的缝隙刺入车内,距离毡毯上阵痛分娩的太子一寸之隔。
车帘被猛地拉起,刺眼的光落进来,一道金边滚在殷明垠冷汗涔涔的苍白脸颊,将他鸦羽般的长睫染成金色。
一个面目狰狞的北狄兵趁乱钻了进来,拉起车帘,贪婪的目光落在车内的人身上,一时愣住了。
只见宽敞的马车内铺着厚实华丽的毡毯,姿容昳丽的美丽少年衣袍凌乱,小腹浑圆地凸起,躺在毡毯上正痛苦无力地分娩,身下濡湿一片。
即便是痛苦的表情,也能看出他生得太过漂亮,又怀孕大着肚子,极具女子的特征,以至于这个北狄兵一时辨不清他的身份,只觉得眼前一幕太过震撼,举着刀愣在原处。
刺眼的光使殷明垠缓了几秒才看清眼前景象,他在看清对方的一瞬瞳孔收缩,唇中急喘,身上盖着的披风早已凌乱地落下去,露出他孕子待产的腹部,就在这极其痛苦的分娩过程中被对方发现了秘密。
他无处可逃,胸膛惊惶地起伏,无力地护住肚子,挣动着双腿往里缩动,沾湿的衣袍下摆拖过毡毯,残留下羊水的痕迹。只可惜,在这刀剑环伺的马车内不过徒劳。
那名北狄兵受到短暂的冲击后,很快辨认出他的身份,何况就算不是太子,这马车里的人也万万不可放过。
他眼里凶相毕露,举起弯刀砍了过去——
“啊啊啊……!”惨叫声惊起,血溅上毡毯,殷明垠双颊惨白,蜷身护着肚子。
他紧阖的眼颤巍巍抬起,只见那个北狄兵腰部断裂,露出内脏骨头,被马车外飞掠而过的刀影当场腰斩,剩下的上半截身子双手抓扯,像案板上斩断的鱼头滑下了马车去。
殷明垠胸膛起伏,如释重负瘫软在地上,阵痛又起,仿佛一双大手在他腹中揉捻,势要将成熟的孩子推出体外。
“唔呃——”他漂亮的脖颈紧绷,喉结起落,身下濡湿更多,逐渐混着血迹,将毡毯染红。他蜷紧了身,死死捧住肚子,像穷途末路的小兽生生捱着碾肉拆骨的剧痛,喉中发出碎裂的痛吟,一次次用力。
其间不断有中原士兵和焉须月手下的北狄兵赶来帮忙,马车外尸骨如山,顾西瑗被一大群人缠着,分身乏术,不时掷出弯刀清理马车周围的敌兵。
这般状况下僵持许久,生生未能让焉兰郁的北狄兵突破防线,有些北狄兵急于抓人立功,怒吼着开始撞击马车,试图将它掀翻,迫使里面躲藏的人出来。
“太子殿下……!”弘遂自顾不暇,眼睁睁看马车被掀得倾斜起来,就要翻倒过去。
车厢壁和车顶上还插着不少北狄弯刀,刀刃向里,整个车厢扎得像刺猬一样。马车一旦翻倒,里面的殷明垠撞上车厢壁,立刻会被刀刃贯穿,断无生路!
“太子妃——”他的声音嘶哑,下意识向着顾西瑗嘶喊,“救救殿下!马车要翻了——”
殷明垠卧在被血浸透的毡毯上,他脸颊如雪,唇瓣干瘪,已经在产痛中奄奄一息。
殷红的血染透了他竹月色的衣袍,侧卧的姿态,可见他的上腹干瘪下去,腹底却更显着地凸起,孩子已经露头了,他的体力耗尽,正在阵痛的间隔积蓄力气。
马车就在这时剧烈震颤起来,整个车厢都开始震动倾斜!
殷明垠虚软无力的身子就这样随着马车的倾斜,无法控制地滑向车壁。
车壁上扎着密密麻麻的刀尖,尖端正对着他的眼睛、肚子和双腿,一旦滑过去,他会被全身戳穿,扎在那车壁上,变成一个血人,肚子里尚未诞下的孩子也会当场死亡。
北狄兵的咆哮从车外传来,马车几乎倾斜过半,殷明垠精疲力竭地看着越来越逼近的刀尖,惨白的指尖按紧了肚子。生死关头,他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但他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抽空了力气才生出孩子的头,如今只差一点点……
少年太子满额冷汗,墨黑如缎的长发紧贴着他如雪的肌肤,他看着不断迫近的刀尖,看清了自己的宿命,身体无法控制地向前方滑落。
他伸出手,手臂重重撑住车壁,阻止自己往前滑去,徒劳地争取一点时间。